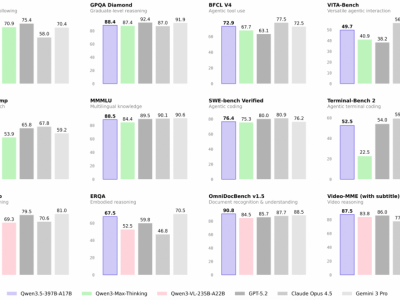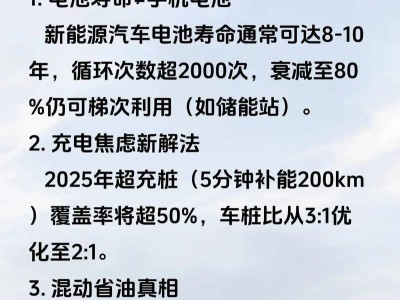当新春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一声清越的嘶鸣自历史深处传来——丙午马年,正以昂扬的姿态踏春而至。这匹承载着千年文明的生灵,从青铜器的纹路中跃出,在边塞诗的苍茫里奔腾,最终化作新春扉页上跃动的墨痕,将开拓、忠义、自由与奋进的精神,镌刻进民族的基因。
在冷兵器时代的烽烟里,马是力量的具象化符号。汉武帝为求“天马”远征大宛,不仅为帝国带回血统纯正的骏马,更让“天马行空”的意象升华为民族对自由与力量的浪漫想象。河西走廊的马蹄声里,驮负着战士与粮草,更驮负着一个新兴王朝开疆拓土的雄心。项羽的乌骓在垓下被围时仍不离不弃,当霸王唱出“时不利兮骓不逝”的悲歌,马的忠诚已超越生物本能,成为中华文化中“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图腾。关羽的赤兔马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护送二位嫂嫂,它的每一次奋蹄都在诠释“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信条,与主人共同被奉为忠义的化身。
当战火暂歇,马蹄声化作连接文明的纽带。张骞使团的马队穿越大漠,带去东方的丝绸与技术,带回西域的物种与艺术,在地理与心理的屏障上凿出第一道裂缝。玄奘的白马驮着佛教经典穿越雪山荒漠,十七载寒暑的蹄印连接起那烂陀寺的晨钟与长安大雁塔的暮鼓,见证了佛教文化与中国思想的深度融合。丝绸之路上的马帮,不仅负载着商品,更在亚欧大陆的腹地踏出流动的文明血管,让王维笔下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与岑参的“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成为跨越时空的共鸣。
在文学艺术的殿堂里,马挣脱了肉身的束缚。李贺的《马诗》中,“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的清冷里迸发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杜甫笔下的胡马“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将忠诚与信任化作骨相峥嵘的意象;陆游梦中的“铁马冰河”,则是报国初心在风雨交加之夜的呐喊。绘画领域,韩幹的《照夜白图》以丰腴体态展现大唐气象,郎世宁的《百骏图》用光影明暗融合中西技法,徐悲鸿的奔马则以酣畅笔墨成为民族觉醒的号角。这些艺术形象,让马成为人格理想、时代精神与民族气质的璀璨投影。
在民俗信仰中,马是传递美好的使者。春节的春联与窗花上,“马到成功”“龙马精神”承载着对事业顺遂的期许;“一马当先”赞扬着开拓者的勇气,“千里马与伯乐”的典故则探讨着人才与识才者的关系。婚姻礼俗中,“白马王子”的意象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美满姻缘的向往巧妙结合,社火表演里的“马舞”“跑竹马”以欢快形式演绎着马的故事,让这一生灵从图腾与艺术中走下,成为百姓生活中可感可触的欢乐元素。
关于马的寓言,是穿越千年的智慧结晶。“塞翁失马”通过福祸相倚的转换,诠释着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的辩证思想;“田忌赛马”展示以智慧谋略取胜的智慧;“老马识途”则强调经验在应对未知时的价值。这些短小精悍的故事,为现代人提供着永恒的处世启迪。
站在新年的起点,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的骑手与骏马。需以“骏马之目”看清方向,不被眼前得失所困;以“良马之足”踏实积累,相信时间的力量;以“战马之胆”勇毅担当,直面未知的挑战;以“天马之思”创新求变,突破常规的束缚。当清脆的蹄声成为奋进的鼓点,当奔腾的身影化作春天的风景,我们终将在时代的原野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