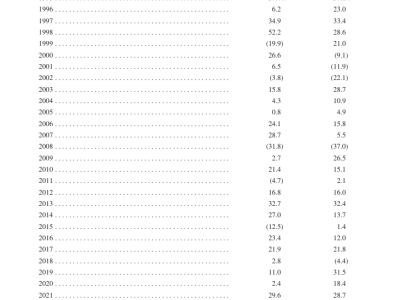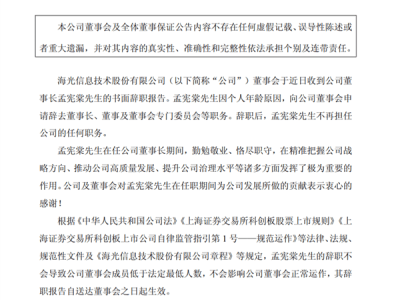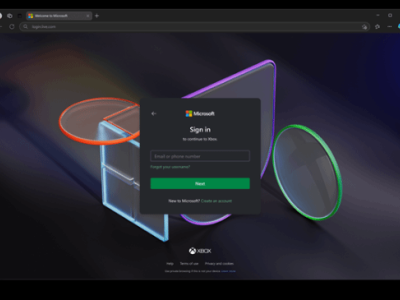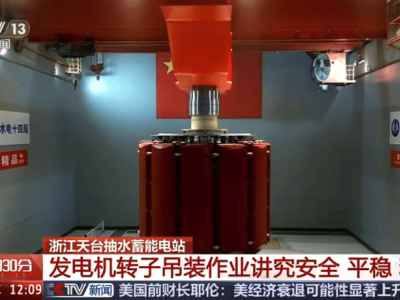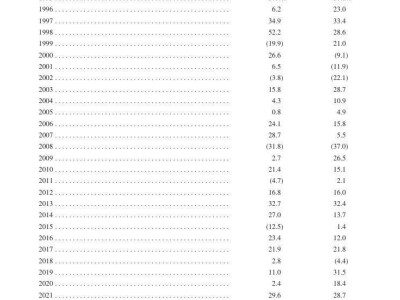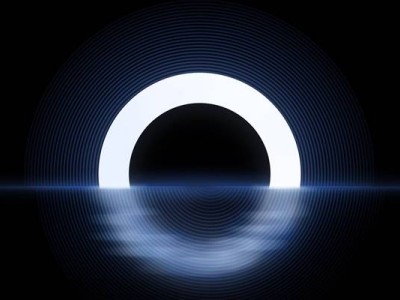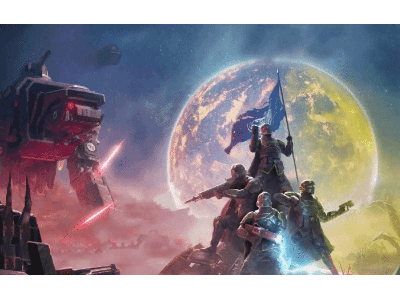在新能源领域的激烈竞争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瑞浦兰钧,悄然在2024年户储电芯出货量全球榜单中跃升至第二位,其背后的支持者竟是钢铁巨头青山集团及其创始人项光达。
项光达,这位中国钢铁首富,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布局新能源领域,将目光投向了储能市场。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与行业领头羊宁德时代一较高下。这一决定看似突兀,实则早有预兆,因为青山集团早已在电池材料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青山集团的故事始于1988年,当时项光达在浙江温州瓯江口的一片滩涂上建立了青山特钢。这个总投资仅300万元的小厂,在宝钢、鞍钢等国有巨头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然而,凭借一项被称为“点石成金”的工艺创新——RKEF镍铁冶炼技术,青山集团成功将不锈钢原料成本降低了40%,并在2003年将不锈钢产能提升至100万吨,占据了当时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2009年,项光达在印尼的一次考察中发现了全球红土镍矿的巨大潜力。印尼拥有全球18.7%的已探明红土镍矿储量,但开发率却不足5%。于是,青山集团联合八家中国企业在印尼Morowali投资47亿美元,建设了全球首个“镍矿-发电-冶炼-轧制”一体化工业园。这个项目仅用28个月就实现投产,年产300万吨不锈钢的热轧卷板直接出口欧美,被当地称为“中国速度”。
青山集团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继续深化产业链布局。2015年,面对中国钢铁产能过剩的严峻形势,项光达提出了“三个三分之一”理论,即未来青山的利润将三分之一来自钢铁、三分之一来自新能源、三分之一来自衍生投资。这一战略转型的背后,是青山集团在电池材料领域的意外发现:采用青山镍铁制备的三元前驱体,振实密度比行业标准高出15%。
2016年,在与宁德时代的技术交流会上,对方采购总监的一句话点燃了项光达心中的火花:“你们要是能做电池,成本能比我们低两成。”这句话成为了瑞浦兰钧诞生的催化剂。随后,青山集团迅速行动,通过一系列股权置换和收购,构建了“镍-锂-钴”三角布局,使得瑞浦兰钧在碳酸锂价格暴涨时,原材料成本比同行低37%。
瑞浦兰钧的储能电芯在市场上迅速崭露头角。其首款280Ah电芯采用的“短极耳+多极组”设计,使内部阻抗降低40%,循环寿命高达12000次,比宁德时代同类产品高出2000次。在市场开拓方面,瑞浦兰钧避开了德国主战场,转而支持意大利经销商推出“电池+逆变器+安装服务”套餐,凭借其独创的模块化设计和比Sonnen低25%的定价,抢下了南欧12%的市场份额。
在产能扩张方面,瑞浦兰钧同样展现出了惊人的“中国速度”。广西梧州50GWh基地从开工到投产仅用11个月,得益于完全复刻印尼工业园的“垂直整合”模式。这种模式使得瑞浦兰钧的制造成本在2023年第一季度降至0.48元/Wh,同期宁德时代为0.57元/Wh。
然而,新能源产业的竞争远不止于电池性能和制造成本的比拼。宁德时代凭借巨额的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在电池能量密度、低温性能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面对这样的技术代差风险,瑞浦兰钧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在储能领域,循环寿命和安全性比能量密度更重要。通过改良电解液配方和优化极片压实密度,瑞浦兰钧的280Ah电芯在45℃高温循环测试中,容量保持率比宁德时代同类产品高出8个百分点。
产业链布局的差异也是两家企业竞争的关键。宁德时代在德国建立了海外研发中心,专注于高镍体系开发;而瑞浦兰钧则在印尼打造了“采矿-冶炼-前驱体”一体化基地,镍原料到厂价比宁德时代低40%。这种优势在镍价波动时尤为突出,使得瑞浦兰钧在价格上更具竞争力。
在回收体系的建设上,两家企业也展现出了不同的战略思维。宁德时代在全国布局了2300个回收网点,深入县级市场,通过“以旧换新”模式提升了退役电池的回收率。而瑞浦兰钧则与法国苏伊士集团合作开发了湿法回收工艺,虽然网点数量较少,但锂回收纯度高达99.9%,较行业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深入,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宁德时代和瑞浦兰钧之间的较量,已经从简单的市场份额争夺升级为全产业链生态的全面对抗。这场没有硝烟的竞赛,不仅考验着两家企业的技术实力和市场策略,更将重新定义新能源产业的未来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