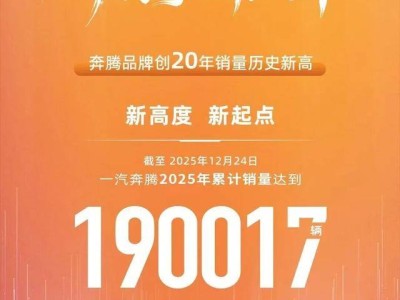高空风能开发正成为全球能源领域的新焦点。2025年9月,北京临一云川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S1500浮空器在新疆完成首飞试验,这款采用气球构型的系留浮空器专为空中风能捕获设计,标志着全球首个兆瓦级商用浮空风力发电飞行器正式诞生。与此同时,由中国能建中电工程牵头的"大型伞梯式陆基高空风力发电关键技术及装备"项目也取得突破,其5000平方米的"空中捕获伞"启运内蒙古进行高空风能测试。此前,中国能建在安徽绩溪投资建设的高空风能发电示范项目已于2024年实现装机并网发电。
高空风能(AWE)系统通过空气动力或静力设备直接捕获风能并转化为电力或机械牵引力。这项技术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英国发明家乔治·波科克的Charvolant风力越野车,其利用两个400米长的风筝驱动车辆运行。近现代以来,AWE技术逐渐向发电领域延伸,特别是在能源需求增长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背景下,高空风能因其资源丰富、分布广泛的特点受到各国重视。与传统地面风电机组相比,AWE系统具有材料需求低、部署灵活、可利用高空稳定风能等优势,据研究显示,某AWE系统相比同等功率的传统风电机组可减少超过70%的材料使用。
目前AWE技术主要分为空基发电和陆基发电两种模式。空基发电将发电机直接安装在飞行器上,通过系留电缆传输电力;陆基发电则利用飞行器在高空飞行产生的动力拉动地面发电机。从构型来看,主要分为浮空器型和侧风风筝型。浮空器型如系留气球和旋转气球,通过浮力支撑发电设备,但体积较大;侧风风筝型则利用软体或硬体风筝的侧风飞行产生动力,通常采用8字或螺旋轨迹飞行。例如,德国SkySails公司开发的软体风筝系统,通过高性能纺织品制造的伞形动力风筝,配合地面绞盘和发电机,已实现近100千瓦的持续发电。
在技术发展方面,欧美国家起步较早。美国Altaeros公司曾开发浮空涡轮系统,在阿拉斯加实现30千瓦发电;法国Wind Fisher公司探索马格纳斯效应转轮技术;谷歌旗下的Makani公司则研发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虽因商业化困难于2020年关闭,但其技术数据推动了行业进步。挪威Kitemill公司开发的垂直起降无人机采用陆基发电模式,通过螺旋上升式运行实现100千瓦平均功率发电,并获得欧盟多次资助。欧洲的SkySails、Airseas和Kitepower等公司也在软体风筝领域取得进展,其中Airseas为空客运输船开发的"海翼"系统,利用1000平方米的风筝提供推进动力,显著减少碳排放。
中国在高空风能领域的发展后来居上。2023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新型高空风力发电关键技术及装备"项目,推动浮空涵道涡轮和伞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发展。临一云川能源技术公司成立两年内推出三款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其中S1500采用40米直径环形涵道和12台风涡轮机,在1500米高空实现兆瓦级发电,计划2026年量产。中国能建则聚焦伞梯式陆基发电,其安徽绩溪示范项目利用300米至3000米高空风力发电,2025年1月实现1000米高空100千瓦发电。新研发的氦气球伞梯组合体将5000平方米做功伞拉升至3000米高空,通过碳纤维缆绳驱动地面发电机组,预计2026年批量投产,每年可减少碳排放4000吨。
高空风能技术的推广面临多重挑战。从技术层面看,需解决航空器设计、感知控制、材料制造等关键问题;从管理层面看,AWE系统兼具航空器和能源基础设施属性,需协调空域划分、运行冲突、适航性审查等跨领域问题。例如,如何为不同高度的AWE系统规划风场空域,如何进行安全性审查,这些问题尚无定论。尽管如此,随着材料科学、人工智能和数字孪生技术的进步,AWE系统的控制可靠性和运行效率正在显著提升,为其规模化应用奠定了基础。
在应用场景方面,中小型AWE系统可服务于偏远地区、海岛、野外军事设施等特殊场景,提供独立电力供应;大型系统则可与传统风电场结合,在不额外占用土地的情况下提升单位面积风能捕获能力。AWE技术还可为航空业碳中和提供支持,如为氢燃料生产设施供电、为偏远机场提供电力、为电动航空器充电等。随着技术不断成熟,高空风能有望成为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