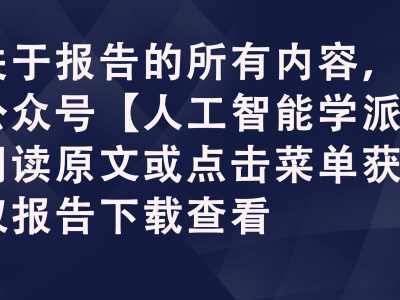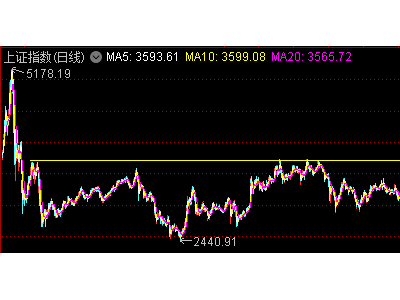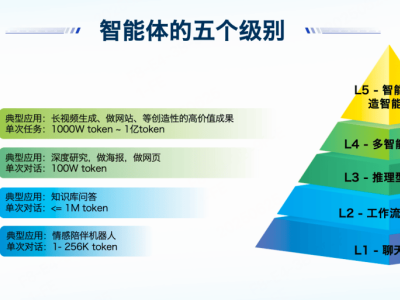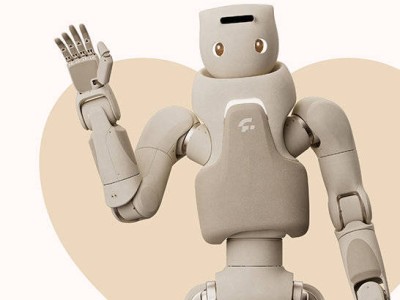盒马X会员店的退出,标志着其向Costco和山姆发起挑战的中产梦想破灭。2024年8月,随着最后一家门店的关闭,这场零售实验以全面撤退告终。从2023年的价格战喧嚣,到一年后的黯然离场,盒马会员店的故事成为中国新零售行业的警示案例,揭示了该行业的严酷生存现实。
首要问题在于盒马会员店的定位模糊。它试图同时走高端会员制路线和低价策略,这种自相矛盾的战略,如同在茫茫商海中失去了罗盘的船只。以北京建国路店为例,该店位于CBD核心区域,租金高昂,本应主打高端市场,却推出了与本土消费习惯不符的大包装商品。结果,开业首月客单价仅为600元,远低于山姆的1500元水平,最终在短短7个月内关门大吉。

服务层面,盒马会员店同样存在显著短板。消费者需凑单满199元才能免运费,且配送时效仅为次日达,相比之下,山姆提供2小时极速达服务。年费方面,盒马与山姆持平,均为258元,但其会员权益的不稳定性导致续费率大幅下滑。消费者支付会员费后,未能享受到相应的服务,“高端定价、低端体验”的矛盾,使得会员费的价值感大打折扣。
盒马在本土化方面的不足和资源内耗问题同样突出。中国家庭结构小型化与大包装商品存在天然矛盾,而盒马并未对此做出针对性调整。其自有品牌“盒马MAX”占比仅为20%-40%,远低于山姆60%的水平,甚至出现了同厂商品价格倒挂现象,社交媒体上关于“付费买贵”的吐槽不绝于耳。

多线作战进一步分散了盒马的资源。会员店作为“一号工程”,在与盒马鲜生、盒马NB(邻里店)的竞争中逐渐败下阵来。2023年的价格战虽然带来了247%的销售额增长,但利润被大幅压缩,运营体系几近崩溃,如北京世界之花店在闭店前已出现货架空缺、试吃取消等问题。
赛道挤压也是盒马会员店面临的严峻挑战。山姆在两年内新增11家店至47家,Costco的本土化供应链也日益成熟。这些国际巨头凭借深厚的全球采购网络和成熟的会员体系,构建了后来者难以超越的规模壁垒。而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数据显示,会员店仅占社零总额的0.1%,有限的中产客群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盒马既未能突破规模瓶颈,又错失了下沉市场的机遇。

盒马的退出,或许并非故事的终点。其在社区店转型中探索的“菜场改造”模式,在二三线城市展现出新的可能性。某三线城市店主表示,将帝王蟹换成活鱼现杀后,单店日销量反而增长了三倍。这或许预示着,中国零售的突破口,或许不在于盲目模仿Costco,而在于发掘符合本土需求的“菜场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