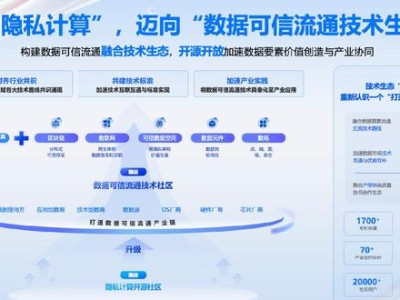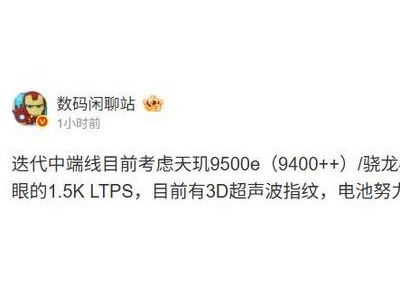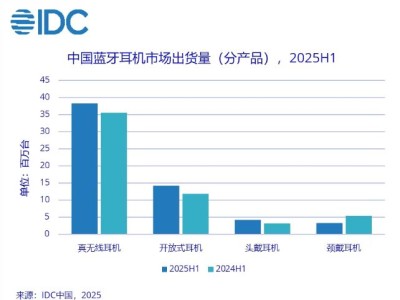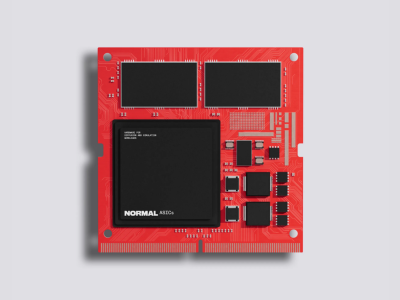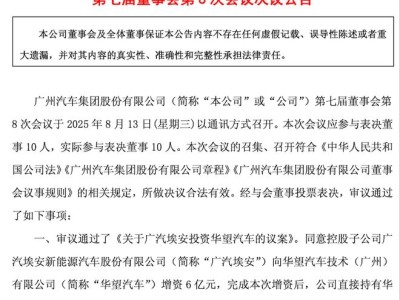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盛大开幕式上,拳王阿里以颤抖的双手点燃了圣火,这一幕震撼了全球数亿观众。阿里,这位昔日的拳击传奇,其双手曾因迅猛的拳法而名震世界,如今却因帕金森病(PD)的侵袭而失去控制。圣火的熊熊燃烧,不仅象征着奥林匹克的荣耀,也悄然映照出人类与帕金森病斗争的漫长历程。
帕金森病,这一在中老年人群中肆虐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被誉为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老二”,是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第三大杀手”,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从最初被误认为是衰老引起的震颤,到如今全球超过1000万患者面临的沉重负担,人类在药物研发的道路上已跋涉半个多世纪,却始终未能找到根治的“金钥匙”。
帕金森病的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跨越古印度、古希腊乃至中国的医学典籍。然而,直到1817年,英国医生詹姆斯·帕金森才首次系统归纳了这种疾病,并描述了其核心特征:静止性震颤、肌肉僵直、运动迟缓和姿势失衡。尽管他的开创性论文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但法国神经学之父Charcot后来重新审视了这些症状,并正式将其命名为“帕金森病”。
进入20世纪,科学家们开始对帕金森病的病理机制进行深入探索。1912年,德国神经病理学家Fritz Lewy在患者大脑中发现了路易小体,而前苏联学者Konstantin Tretiakoff则锁定了中脑黑质为病变的核心区域。这些发现逐渐揭示了帕金森病的病理基础:黑质中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大规模死亡,导致纹状体中多巴胺浓度锐减,从而引发震颤、僵硬、动作迟缓等症状。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帕金森病远比想象中复杂。路易小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由α-突触核蛋白错误折叠形成的蛋白团块,这些蛋白团块如同细胞内的“定时炸弹”,不仅直接损伤神经元,还会通过神经连接扩散至健康细胞。帕金森病的发病机制涉及遗传与环境因素的交织,约10%的患者携带明确致病基因突变,而90%的散发性患者则受环境因素影响,如长期接触农药、重金属等。
这种隐匿的进展使帕金森病成为老龄化社会的一大威胁。在我国,65岁以上人群的患病率高达1.7%,80岁以上人群则超过4%,总患者数已突破300万,占全球近半数。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数字还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不断攀升。
在治疗方面,尽管左旋多巴的发现曾一度让医学界看到了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疗效逐渐减弱,甚至引发“开关现象”和“异动症”等副作用。科学家们虽然开发出了一系列辅助药物,但这些药物本质上仍是对多巴胺系统的“修修补补”,无法从根本上治愈疾病。
新药研发的困境源于帕金森病病理机制的复杂性和临床转化的多重壁垒。尽管全球现有超百款药物处于临床阶段,但近十年来III期临床试验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靶点验证的艰难、血脑屏障的阻碍、临床前模型的局限性等因素,都增加了新药研发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然而,尽管挑战重重,全球研发管线仍在缓慢推进。在生物药领域,α-突触核蛋白已成为最有希望的靶点之一,多款抗体药物已进入II期临床。在小分子领域,针对LRRK2激酶的抑制剂备受关注,显示出在携带LRRK2突变的患者亚群中延缓神经元损伤的潜力。基因疗法和细胞疗法等前沿疗法也在积极探索中,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帕金森病的疾病进程。
在国内,虽然帕金森病药物研发起步较晚,但正以差异化路径寻求突破。上海纽赛尔生物的自体iPSC源多巴胺神经元产品、恒瑞医药的新型长效左旋多巴制剂、绿叶制药的罗替戈汀缓释微球注射剂等,都在为帕金森病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提前诊断与早期干预被认为是突破帕金森病治疗困局的关键。近年来,科学家们发现肠道菌群紊乱、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等前驱期标志物,可提前预警帕金森病。德国基尔大学团队通过血液α-突触核蛋白种子扩增试验,能在确诊前检测到异常,为超早期干预提供了可能。
帕金森病药物研发的困境,本质上反映了人类对大脑复杂性认知的局限。从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然而,随着多学科协作的加强和AI技术的赋能,科学家们正逐渐揭开帕金森病的神秘面纱。未来,随着基因编辑、细胞疗法等技术的不断进步,那把根治帕金森病的“钥匙”或许终将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