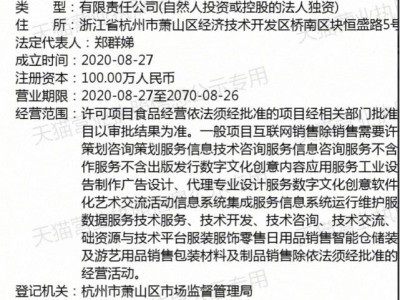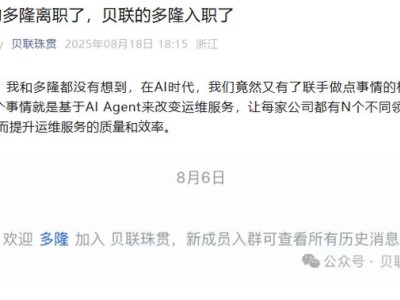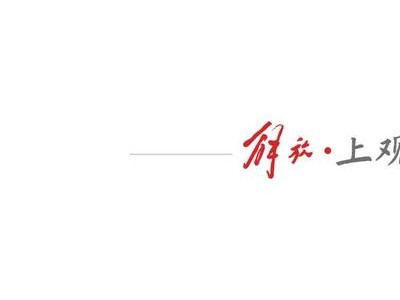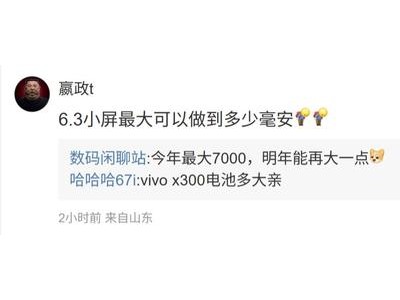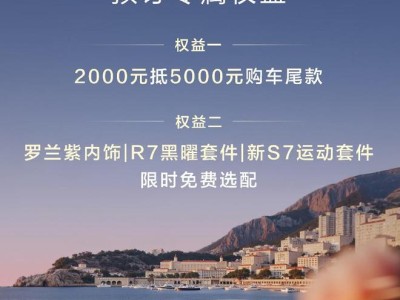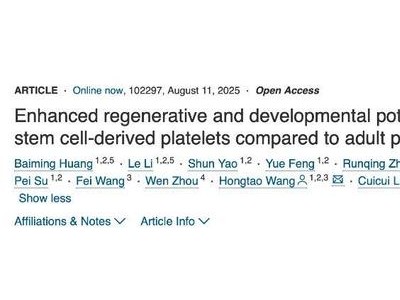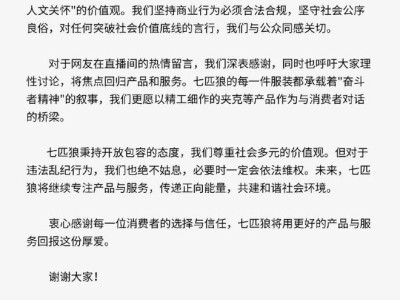在宇宙的广阔舞台上,有一个令人着迷的概念——“一光年”,它描绘的是光在真空中无阻碍地行进一年的距离,换算成具体的数字,大约是9.46万亿千米。然而,当我们尝试从光的独特“视角”去审视这一距离时,一个看似矛盾却又充满哲理的画面浮现出来:对人类而言代表漫长岁月的一光年,对光来说却仿佛是转瞬即逝的“瞬间”。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光年”这一概念的出发点——它是基于地球这个“静止参考系”所定义的距离。在日常经验中,我们通过时钟计量时间,用标尺或电磁波测定距离,因此,“光飞行一光年耗时一年”的说法,是在地球这一相对静止的参照物下得出的结论。
但光的身份与众不同,它打破了常规逻辑的束缚。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揭示了光速在真空中的绝对性,无论观测者的运动状态如何,光速始终恒定在每秒30万千米。更引人深思的是,当物体的运动速度趋近于光速时,会出现“时间膨胀”与“长度收缩”两大奇异现象,而光,正是这些现象的终极体现。
“时间膨胀”意味着,随着物体运动速度的提升,时间的流逝速度会相应减慢。这一物理规律并非空穴来风,1971年的实验便是明证:科学家将原子钟分别置于地面和高速飞行的飞机上,结果发现,飞行结束后的飞机上原子钟比地面上的慢了约59纳秒,与相对论预测的结果高度一致。当速度达到光速时,时间膨胀效应达到极限,从地面观测者的角度看,光的时间仿佛静止了,出发与抵达的瞬间融为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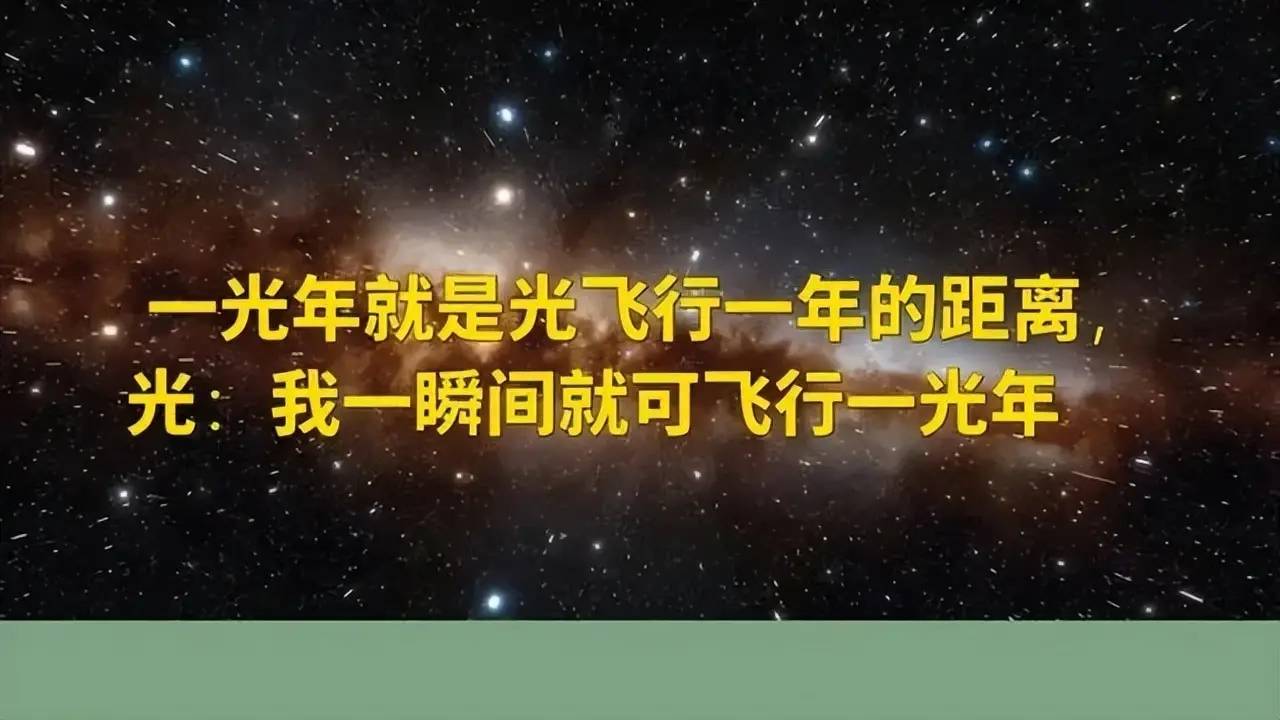
与此同时,“长度收缩”现象也让人叹为观止。随着物体运动速度的增加,其在运动方向上的长度会逐渐缩短。以光速为例,从地面观测者的视角来看,那看似遥远的9.46万亿千米的一光年距离,在光的“眼中”却被压缩至极致,长度归零。对光而言,穿越这一距离就如同跨越一个无长度的点,瞬间即可完成。
这种观测者视角的差异,实则反映了相对论中“时空一体”的深刻内涵。在爱因斯坦的理论框架下,时间和空间不再是孤立的两个概念,而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时空整体。
值得注意的是,“光的视角”更多地是一种理论上的构想,而非实际可感知的体验。因为根据相对论,只有静止质量为零的物体(如光子)才能达到光速,而有静止质量的物体,则无法逾越这一速度极限。将一千克的物体加速至光速,理论上需要无穷多的能量,这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
然而,理解“光的瞬间与人类的一年”这一对比,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光年”这一宇宙尺度的概念,更能让我们领略到宇宙时空的奇妙与深邃。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距离地球10光年的恒星时,其实是在目睹它10年前的模样。光从恒星出发,历经人类时间尺度上的10年旅程,却在自己的“时间”里实现了瞬间的跨越。这种跨越时空的“延迟影像”,正是相对论时空观在宇宙中的生动展现。
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到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理论,人类对时间与空间的认知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一光年,在人类眼中是浩瀚宇宙中的漫长距离,在光的视角里却是瞬间的跨越。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揭示了宇宙时空的本质:时间与空间并非绝对,一切观测结果都取决于观测者的运动状态。这一认知,无疑是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理解宇宙本质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