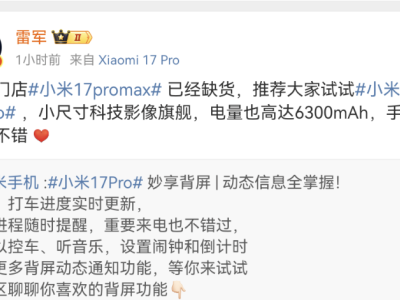十年前,3D打印设备还只是科技极客的“实验玩具”。受限于打印速度和精度,这类设备难以满足工业化生产需求。当时,全球3D打印市场被欧美企业主导,Stratasys等厂商凭借专利壁垒长期垄断设备供应。直到2008年前后,随着核心专利到期,中国厂商依托完整的供应链优势进入市场,通过亚马逊、速卖通等平台向全球销售低价套件产品。然而,这些设备需要用户自行组装数十小时,打印速度仅维持在每秒50毫米的水平,仍停留在“手工时代”的初级阶段。
“行业真正的瓶颈不在于能否打印复杂模型,而在于能否通过提升速度成为真正的生产工具。”潮阔创始人申康指出。他观察到,过去十年间3D打印设备虽在教育和爱好者市场普及,但始终未能突破生产力门槛。以单日仅能生产数个零件的设备为例,本质上仍是“玩具”而非工业工具。
2015年,从阿里巴巴离职的申康创立潮阔,押注3D打印行业的效率革命。初期,公司通过销售低价套件实现短期盈利,2017年“双十一”单日销量突破千台。但就在行业红利期,申康做出一个激进决定:砍掉最畅销的机型,全力投入高速打印技术研发。这一决策在公司内部引发强烈反对,因为当时全球95%的3D打印机仍采用成本低但性能有限的I3架构,而潮阔选择的技术路线——三角洲架构,因三轴并联设计导致算法复杂度呈指数级增长,研发难度极高。
经过三年技术攻关,潮阔在2019年推出首款高速样机,并于2020年正式发布SR系列,将打印速度提升至150毫米/秒,首次验证了高速路径的可行性。2022年,V400机型问世,以600毫米/秒的速度推动行业进入“动车时代”。这一突破直接催生了海外“打印农场”的兴起,批量生产手办、灯具等商品的小型工坊,依托效率提升将单件打印时间从数小时压缩至几十分钟。
2024年成为行业转折点。潮阔发布的迅影光S1 Pro以1200毫米/秒的速度刷新纪录,被权威机构认证为全球最快消费级FDM 3D打印机。该机型将模型打印时间从两小时缩短至五十分钟,迅速在北美和欧洲创客社区走红。同年,中国3D打印机出口量达377.8万台(不含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长32.75%,占据全球96%的消费级市场份额。其中,售价2万美元以上的专业级设备出货量却出现下滑,印证了消费级市场的高速增长趋势。
需求端的变革更为显著。如今超过80%的3D打印机被用于实际生产,而非个人娱乐。以潮玩经济为例,义乌等地涌现出数千台规模的“打印农场”,生产效率的跃升直接改变了商业模式。过去打印一条30厘米的龙形摆件需十几个小时、售价近千美元,现在使用潮阔高速机仅需1小时,成本降至五百多美元,回本周期缩短十余倍。这种效率革命不仅重塑了潮玩产业,更在灯具、医疗支架、Cosplay装备等领域催生出新业态。随着PLA材料价格从每吨三万元降至两万元以下,单个手机支架的打印成本已不足一元,应用场景持续扩展。
在技术层面,高速打印带来的挑战远超想象。从最初的A4纸手动调平,到如今在1200毫米/秒速度下保持精度一致性,潮阔用八年时间重构了整个硬件与控制链条。“每提升一倍速度,技术难度就呈几何级增长。”申康透露,公司为此投入了巨额研发资源。这种坚持使潮阔在产品迭代上形成独特优势:从SR系列到V400,再到S系列与T系列,持续突破的速度与稳定性成为差异化核心。
与拓竹、创想三维等竞争对手相比,潮阔的路径更具技术导向。拓竹凭借大疆背景和Kickstarter众筹快速打开海外市场,创想三维则通过丰富的产品矩阵占据用户规模优势。而潮阔选择更早押注高速赛道,通过连续迭代在速度和稳定性上建立壁垒。申康坦言:“高速竞争比低价套件时代残酷得多,但这是让3D打印摆脱‘玩具’属性的唯一路径。”
当前,全球消费级3D打印机市场正经历深刻变革。2025年一季度,该领域出货量首次突破100万台,同比增长22%,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市场。在中国,潮阔已从单纯的硬件制造商转型为技术驱动的产业参与者,其战略重心正转向通过效率提升重构生产工具的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