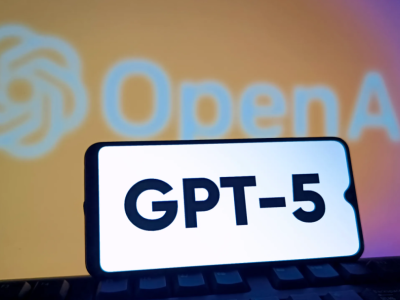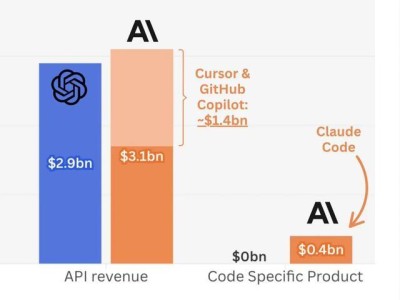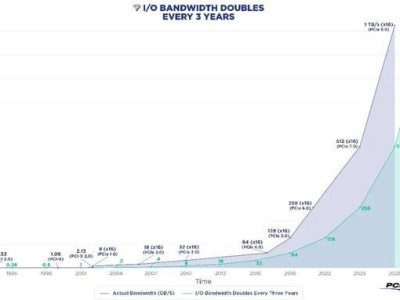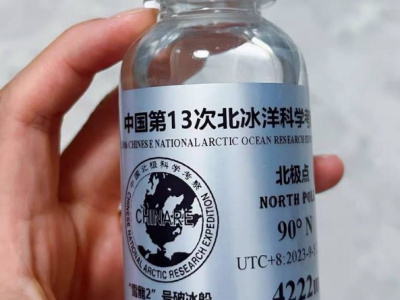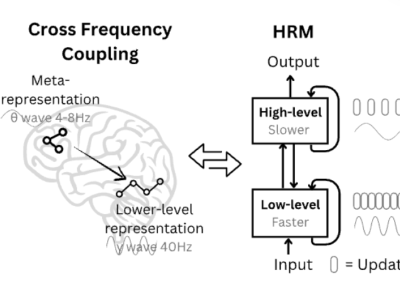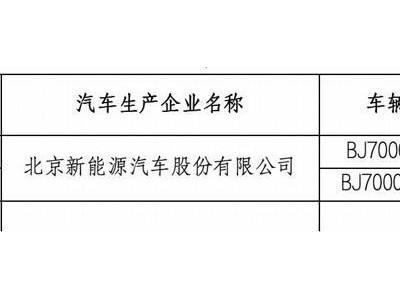民宿业在连续两年的暑期遭遇重创,众多民宿主纷纷发声表达无奈与困惑。去年,“五一”假期与暑期业绩惨淡已让不少民宿主心生寒意,未曾料到,今年的情况更为严峻。
新疆禾木村的民宿主在网络上抱怨:“今年的生意怎么会如此冷清?五六月份预订量就持续低迷,本以为七月能有所好转,结果仍有不少空房。这究竟是怎么了?”类似的困境并非个例,大理作为民宿遍地的地方,民宿主的苦日子更是由来已久。
大理的民宿主雷宝宝在视频中透露,去年四家民宿在“五一”假期时单日营收早早破万,而今年即便增加了一家店,直到7月下旬才勉强破万,平时更是只有8000至9000元的收入,而“五一”期间最高时也仅有6000至7000元。原本预期五家民宿共15个房间在旺季能带来1.2至1.3万元的营收,现在看来这一期望过于乐观。
云南大理、丽江的民宿生意下滑之声不绝,以往洱海边民宿需要提前一个月预订,如今临近出行日期也不愁订不到房间。网红打卡地阿那亚的民宿同样生意惨淡,有业主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七月旺季没有客人,六月出租率较去年下降了一半。
从禾木到大理,再到阿那亚,不论是传统民宿还是高端民宿,生意都不尽如人意。许多民宿老板原本期待暑期能有所回血,现在看来这一愿望恐将落空。暑期的冷清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蒙上了一层阴影。
民宿业的寒冬不仅限于个别地区,整个旅游行业都受到了波及。景区、酒店、南极旅游、研学游等赛道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仿佛整个旅游行业在玩“轮盘赌”,轮流遭遇困境。经济环境的影响最为直接,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下降,家庭旅行支出预算大幅缩减。
面对困境,不少民宿选择以价换量,然而即便如此,收益相比去年仍有大幅下滑。民宿主之间虽互相宽慰,但在订单不佳的情况下,下调价格成为无奈之举。民宿数量激增也是导致行业困境的关键因素之一。数据显示,从2014年至2024年,我国民宿数量从约3万家增长到超过30万家,其中约80%的企业并不盈利。
以某省会城市的民宿为例,七月份仅有两三天价格能达到160元,平时价格更低,但经营成本却在170元左右,再加上30多元的赠品成本,即便是亏本也无人问津。阿那亚社区内的民宿同样面临挑战,虽然社区内共有四千多家民宿,但外围还有无数家不受官方指导价限制的民宿,价格参差不齐,导致游客更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优惠的住宿。
民宿行业面临的不仅是市场环境的问题,大众对民宿的热情也在逐渐消退。早期的民宿曾是“诗与远方”的代名词,充满房东的个人特色与温情。如今,商业气息愈发浓厚,人情味却逐渐淡薄。民宿物业从自家房屋转变为租赁物业,热门景区周边的房租成本每年高达30至50万元,加上装修成本等,前期投入轻松超过百万,甚至达到两三百万元。
房租、员工工资、水电费等固定成本居高不下,让不少民宿主难以承受。民宿主们寄望于平台,但平台流量也在下滑,为了吸引更多流量,平台要求民宿打折或提供优惠券。民宿服务设施参差不齐、照片与实际不符等问题也让游客对民宿失去信心,住民宿如同开盲盒,既看运气又看民宿主的良心。
相比之下,连锁酒店因其标准化服务而受到青睐。游客能明确知道花费多少就能享受怎样的服务,这种确定性让连锁酒店更具吸引力。可以预见的是,今年暑期结束后,又将有一大批民宿面临转卖或倒闭的命运。
民宿行业虽不会消失,但市场从增量转为存量后,行业洗牌在所难免。优胜劣汰之下,经营不善、品质低劣的民宿将被淘汰,而真正高品质、适应市场的民宿将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