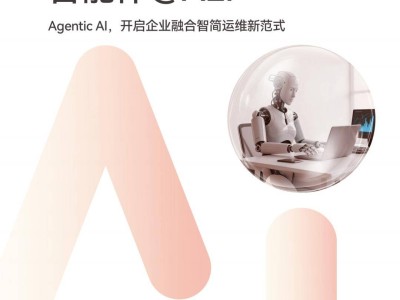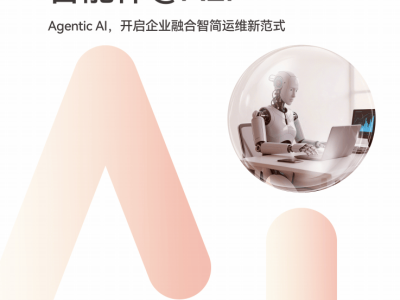中国电商行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作为头部企业的阿里巴巴正面临增长压力与竞争加剧的双重考验。在此背景下,蒋凡的回归与权力集中,不仅是个体职业轨迹的起伏,更折射出这家互联网巨头在战略方向、组织架构和技术应用层面的深度调整。
从“价值观至上”到“业务导向优先”的转变,是阿里巴巴组织逻辑调整的核心特征。2020年,蒋凡因个人事务被取消合伙人身份并调离核心业务,但阿里巴巴并未完全否定其价值,而是将其派往国际数字商业板块。2025财年,该板块收入达1323亿元,同比增长近三成,成为集团增长最快的业务。这一成绩使蒋凡在2024年重返核心管理层,并于2025年进入合伙人委员会,成为最年轻的成员。
这种“起落”背后,是阿里巴巴从强调价值观纯粹性转向以业务结果为导向的实用主义。2023年9月,吴泳铭出任CEO后推行“年轻人提上来、用起来”的用人原则。蒋凡的回归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他兼具技术背景(曾主导手淘“千人千面”算法)和国内外业务经验,完美契合阿里巴巴“聚焦电商、AI驱动”的战略方向。同时,合伙人制度的精简(从26人减至17人,9位元老退出)进一步强化了组织弹性,使决策更贴近业务一线。
在业务层面,阿里巴巴的竞争维度正从“流量争夺”转向“生态协同效率”。2024年11月,阿里巴巴成立电商事业群,由蒋凡统管淘宝、天猫、国际业务、1688、闲鱼等板块;2025年6月,饿了么与飞猪并入该事业群,形成覆盖实物电商、即时零售、旅行服务的超级平台。这种整合通过协同效应,将阿里巴巴原有的资源沉淀转化为结构性优势。例如,淘宝闪购与饿了么的整合带来日均8000万单的订单量,同时通过高频消费提升用户黏性,带动淘宝DAU大幅增长。
生态协同的关键在于构建供给侧壁垒。蒋凡通过整合阿里巴巴的供应链、物流与数据能力,形成“立体零售网络”。在近场零售中,淘宝闪购的“闪电仓”已突破5万家,25%的供给直接来自阿里生态;在远场电商中,天猫品牌线下门店接入闪购体系,实现“线上下单、门店发货”。这种整合使阿里巴巴具备任何单一平台难以复制的优势:外卖起家的平台缺乏电商基因,传统电商平台则缺乏即时履约网络。
效率提升是生态协同的终极目标。蒋凡在阿里巴巴内部发起“成本重构”战役,通过规模效应与科技赋能优化UE(单位经济模型)。例如,淘宝闪购通过订单密度提升与客单价增长,单均履约成本显著下降;AI调度系统将配送时效压缩至分钟级,成本大幅降低。这种效率优化不是简单的补贴战,而是通过运营升级实现结构性成本优势。据多家媒体报道,蒋凡预测,未来三年闪购和即时零售将为阿里巴巴带来1万亿交易增量,其本质是通过生态协同重构人、货、场的匹配效率。
在技术层面,阿里巴巴正从“业务支持”转向“AI重构内核”。2025年,阿里巴巴宣布未来三年投入3800亿元于AI+云领域,超过过去十年总和。在电商场景中,AI不再仅是优化工具,而是深入供应链、物流、用户体验等环节,成为业务创新的核心引擎。例如,淘宝基于通义千问大模型推出“淘宝问问”AI助手,能理解复杂购物需求,提供个性化推荐;AI工具“生意管家”帮助商家生成商品描述、分析数据,中小商家推广成本大幅下降。
AI对供应链的重构尤为深刻。阿里巴巴将AI技术应用于全链路管理,实现“以销定产”的精准运营。例如,通过分析历史销售数据、季节因素与市场趋势,AI系统预测商品需求,优化库存布局,这种技术赋能使阿里巴巴从“交易平台”升级为“智能零售基础设施”。技术的深度应用,使阿里巴巴在体验与效率上构建了差异化优势。
AI驱动为阿里巴巴打开了第二增长曲线。2025财年,阿里云AI相关产品收入连续多个季度实现大幅增长,云业务占总收入比重有所提升。更重要的是,AI技术成为电商业务的核心竞争力。蒋凡在财报中强调,AI驱动不仅提升了用户体验,还优化了商家效率,例如“全站推广”工具帮助商家提高营销效率。这种技术赋能使阿里巴巴在增长放缓的市场中保持韧性,2025财年淘天集团收入同比增长,扭转了此前增速停滞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