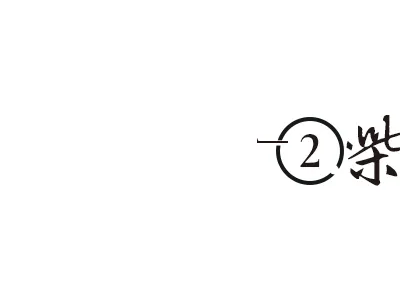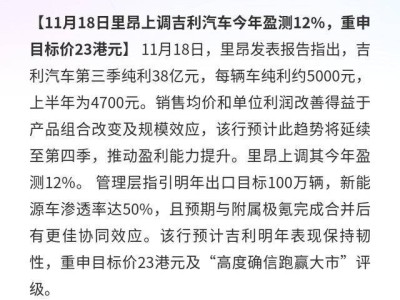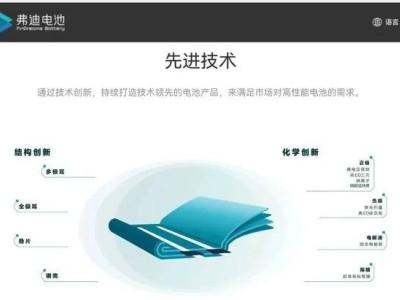人形机器人赛道上,特斯拉与Figure的竞争正从实验室走向公众视野。2025年10月,Figure 03以一支家庭场景一镜到底的演示视频引爆舆论,而同期特斯拉Optimus V3仅释放出金色外壳操作爆米花机的片段。这场“亮相战”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与市场策略的碰撞。
Figure创始人Brett Adcock选择让机器人“先被看见”。在X平台发布的视频中,Figure 03无需人工干预便完成叠枕头、避开宠物、取笔记本等任务,指尖可感知3克压力,手掌嵌入微型摄像头,外层覆盖柔性织物以防碰撞。更关键的是,其自研Helix系统实现了“视觉-决策-行动”的闭环,配合加州BotQ工厂年产1.2万台的产能与Project Go-Big数据集,构建起“真实世界记忆库”。这种“先智能后身体”的路径,让Figure在公众认知中迅速占据“未来生活样本”的定位。
特斯拉的马斯克则延续“系统优先”的逻辑。Optimus V3放弃动作捕捉训练,转向纯视频学习——通过分析人类动作数据训练机器人模仿。为提升算力,特斯拉关闭Dojo训练中心,整合AI5与AI6芯片架构,将资源集中于控制系统。但这种“视觉驱动”的方案面临现实挑战:机器人能“看”却无法“触”,每个失误都需在实体机上反复调试。2025年夏季财报会上,马斯克仅透露原型机在工程总部“24小时走动”,量产计划从原定的2025年底推迟至2026年初。
技术分歧的背后,是两家公司资源禀赋的差异。Figure作为初创企业,没有汽车业务或能源网络的包袱,可全力押注人形机器人。其BotQ工厂采用流水线生产,Project Go-Big数据集通过数千台机器人采集厨房、仓库等场景数据,形成“智能-数据-应用”的正向循环。而特斯拉需平衡自动驾驶、能源存储等多条战线,Optimus项目负责人Milan Kovač的离职与供应链执行器短缺问题,进一步拖慢了进度。截至2025年Q3,特斯拉仓库仍堆积大量未安装机械手的Optimus机体。
马斯克的谨慎源于对“失控”的警惕。在《The All-in Podcast》中,他直言机械手是“整个系统最复杂的部件”,其多自由度协调难度“介于Model X与星舰之间”。2025年6月,特斯拉起诉前员工创立的机器人公司窃取机械手技术,暴露出供应链与知识产权的双重风险。这种对“控制权”的担忧,使其更倾向于“先系统后产品”的路线——即使牺牲市场热度,也要确保机器人可控、可制造、可复用。
Brett则选择“用未来点燃现在”。他在采访中强调,Figure的目标是“让机器人进入世界”,而非停留在实验室。这种思维体现在其快速迭代中:2024年接入OpenAI模型后,Figure 02在厨房整理台面的视频已具备“生活气”;2025年Helix系统上线,BotQ工厂投产,数据集覆盖更多场景。对初创公司而言,抢占公众想象比完善技术更重要——当市场相信“机器人能融入生活”,资本与人才便会自然聚集。
华鑫证券研报指出,特斯拉的“多线并行”导致Optimus进度滞后,但其掌握的能源、制造、供应链能力是产业化关键。当人形机器人进入“百万台级”量产阶段,决定胜负的将不是谁先刷屏,而是谁能让机器人稳定工作。Figure的叙事优势与特斯拉的系统优势,或许会在不同阶段分别主导市场——前者定义“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后者决定“未来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