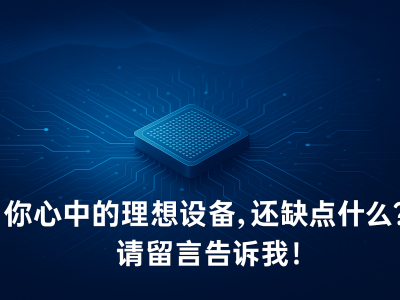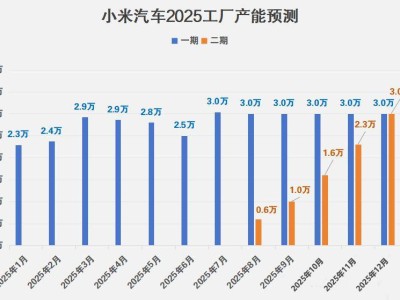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正面临待遇水平偏低的问题,这一现状与《“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要求形成呼应。作为覆盖5.38亿参保人的重要社会保障体系,该制度由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共同构成,其中后者主要面向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财政补贴占比超过85%。如何通过制度优化提升养老待遇,成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课题。
追溯制度发展历程,1986年试点的“老农保”因完全依赖个人缴费导致覆盖率不足15%,最终于1999年退出历史舞台。2014年合并实施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吸取历史教训,引入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的基础养老金,形成“个人缴费+财政补贴”的双支柱模式。数据显示,2024年参保人月均养老金246元,仅相当于农村居民食品支出水平的47%、农村低保标准的41%,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区域差异更为显著,上海城乡居民月均养老金达1651元,而26个省份不足300元,不同群体间待遇差距最高达28倍。
制度设计层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呈现“弱保险、强福利”特征。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多缴多得”的机制不同,该制度中财政补贴占比达85%以上,个人缴费关联性较弱。这种设计虽实现制度全覆盖,但导致待遇水平与经济发展脱节。专家建议将现行“基础养老金”更名为“全民最低养老金”,明确其社会福利属性,并建议中央财政将全国标准从现行123元/月提升至500元/月,使月均待遇达到600元水平。按1.8亿领取人数计算,年需增量资金约8000亿元。
资金筹措方面,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成为可行方案。当前国有企业年度利润总额超6.5万亿元,归母净利润超3.4万亿元,但收益上缴比例长期低于20%,远低于挪威(51.4%)、瑞典(61%)等国水平。若将上缴比例稳定在40%,年可增加财政收入超1.4万亿元,完全覆盖养老待遇提升需求。这种“国资-财政-社保”的联动机制,既能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又能通过增加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释放消费潜力。测算显示,老年夫妻家庭年养老金收入可增加超8000元,增幅达140%,显著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制度升级将产生多重社会效应。全民最低养老金作为养老保障体系的“零支柱”,可为多层次保障体系奠定基础,增强其他层次保障的吸引力。明确福利属性后,制度认同感将显著提升,参保人能更直观感受到国有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区域差异化补贴机制设计,既保证中央财政的公平性,又允许地方根据财力追加补贴,形成“中央保底、地方补充”的可持续模式。这种改革不仅解决当前待遇偏低问题,更为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提供制度保障。
当前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财政承受能力与资金使用效率。虽然国有企业具备盈利支撑能力,但需建立科学的收益评估体系,确保上缴比例调整不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同时,需完善资金监管机制,防止地方配套资金落实不到位。专家建议配套推进个人账户制度改革,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个人增加缴费,形成“财政保底+个人补充”的复合保障模式。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地,将推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向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