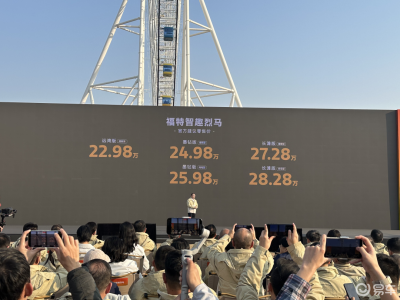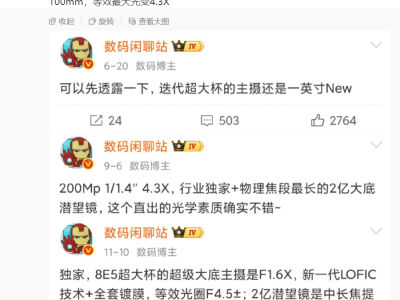镁光灯下,雷勇林——业内更熟悉他“小雷哥”的称呼——正讲述着自己“靠一台机器人月入二十万”的创业故事。他头戴黑色软呢帽,身着笔挺西装,手持麦克风,语气中难掩兴奋。会场外,一排排人形机器人正展示着各自的才艺:有的击鼓,有的唱京剧,有的套着大褂说相声,还有的挥毫泼墨。相比之下,曾经红极一时的跳舞机器人,如今显得有些平淡无奇。
这是一个普通人抓住时代风口、改写命运的故事。今年初,宇树机器人登上春晚舞台表演秧歌,其创始人王兴兴还与任正非、雷军等企业家一同出席了民营企业座谈会,人形机器人由此进入公众视野。二月末,90后的小雷哥斥资三十万元购入一台高配版宇树G1机器人。他随手拍摄的开箱视频意外走红:这个七十多斤重的“铁疙瘩”竟能自行站立,“仿佛木偶被注入了生命,从一滩烂泥变成通电后就能行走的钢铁战士”。
视频的爆火让这台被小雷哥称为“笨笨”的机器人迅速成为日租金八千元的“钢铁员工”。从科技教学到店铺引流,仅用一个多月,小雷哥就收回了成本。随后,媒体报道纷至沓来,越来越多人涌入这个赛道。然而,热潮之下,行业温度已悄然变化。在八分钟的演讲中,小雷哥分享了自己从行业先行者到推动者的心态转变,也谈到了对行业从红利期迈向红海的预判。那些被媒体简化为“租赁遇冷”的报道,以及他更为曲折的低谷经历,却被轻轻带过。
与小雷哥深入交流后发现,过去八个月,他的人生如同坐上过山车,经历了流量狂欢与行业起伏。潮水退去,投机者离场,留下的人开始思考如何坚持长期发展。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也是整个人形机器人赛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的缩影——在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之前,先让人形机器人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生存下来。
从日租一万元到价格腰斩,机器人市场的“祛魅”是否已经开始?作为“钢铁侠”的忠实粉丝,小雷哥一直怀揣着科幻梦想。他从事豪车租赁行业十多年,但近年来新能源车贬值加速,行业价格战激烈,生意愈发艰难。去年底,看到宇树机器人发布的后空翻、跳舞等炫酷视频后,他意识到这个新兴领域可能蕴含巨大商机。于是,他决定投入三十万元购买一台机器人试水——这笔钱在豪车租赁行业不过是一辆好车的成本。
宇树机器人的出现点燃了整个赛道,小雷哥的命运齿轮也随之转动。二月末发布视频后,三月、四月,他带着“笨笨”北上内蒙、西至新疆、南抵海南,足迹遍布中国。婚礼、商演、科技节,甚至乡镇的村超联赛,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媒体跟拍、地方卫视报道,电话响个不停。那时,市场疯狂程度远超想象——机器人供不应求,同行间需要借调设备,客户多到接受拼单。最夸张时,一台机器人一天要赶早、中、晚三场活动,且只能在同城演出,跨城市根本来不及。
“我对这个行业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不少同行是看了我的视频才入行的。”小雷哥说这话时充满自豪,但很快,自豪中又夹杂了一丝苦涩,“结果到后面,连我自己都订不到货了,只能花高价收购。”由于市场狂热,机器人供不应求,宇树G1 EDU版本从官方指导价十六万九千元被炒至二十五万元,U2型号从二十万九千元飙升至近三十万元,且全是期货。四月底,小雷哥在高点加价百分之五十订购了三台宇树G1,盘算着每台机器只要租出去十来单就能回本。前景似乎一片光明,所有人都杀红了眼。
五一假期成为最后的狂欢,将热度推向顶峰。小雷哥的机器人日程全满,单台日租金飙升至一万元。但假期过后,订单量断崖式下跌,“出勤率可能连百分之三十都不到。”他加入的十多个五百人同行群里,大部分人的处境与他相似。更糟的是,他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视频流量和关注度也开始同步锐减。普通大众对机器人是否已经“祛魅”?小雷哥心里没底。
六月,一批同行撑不住,开始退出市场。到了八月,又有一波人选择离场。流量来去如风,媒体开始报道“人形机器人租不出去了”,最火的G1日租金从八千至一万五千元的高位腰斩至五千至八千元。小雷哥真切感受到了寒意,他停止购置新机,只陆续将手中的基础版机型置换为高级版,以求在冷却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与租赁市场的急速降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市场如火如荼。投资人拿着钱四处寻找“下一个宇树”,宇树、乐聚、智元等头部机器人公司在相近时点竞相启动IPO;机器人厂商们不断宣布获得大额订单,争相将机器人送进工厂“实习”,展示商业潜力。行业狂热如潮水般退去,但市场并未消失,只是露出了本有的起伏脉络。尽管机器人租赁业尚未跑完一个完整年度,小雷哥明显感受到这个行业具有淡旺季之分。
进入九月以来,随着各类展会、科技节和校园活动的开展,市场迎来一波回暖。小雷哥的业务重新活跃起来,平均每月能接到十来单,“差不多两三天就有一单”。他粗略估算,前三台机器人应该已经回本。与上半年的狂热不同,随着入局者增多,行业内卷加剧,单台机器的场均租金已从高点回落至五千元左右,甚至能被压到三千元。与此同时,客户的要求也水涨船高。
目前最常见的租赁场景集中在六类:学校科技节、企业展会、宴会迎宾、研学活动、媒体舞台以及商超表演。这些场景的共同点是——需要一个“科技噱头”,一个能让人掏手机拍视频的存在。机器人的表演能力成为最强竞争力。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租赁商们必须提供更多价值。最初的“能动就行”已无法满足客户,现在他们需要定制化舞蹈,甚至开始期待机器人能“直接干活”。“一般场租四五千,定制开发舞蹈就得一万起步。”小雷哥说。但预算通常有限,大多数人还是在现有的成熟舞蹈库里做选择。
面对多元化需求,不同机器人品牌在市场上呈现出清晰的梯队格局。宇树G1仍是最主流的型号——稳定、全能、能跳舞也能对话,被客户广泛认可,是当下的“全能型选手”。但其一米三的身高,在需要“高大威猛”形象的场景中成了短板。智元机器人则凭借其在AI大模型上的先发优势,形成了差异化竞争。其发布的X2型号直接对标宇树G1,强在交互对话能力。小雷哥提到,智元的平台允许用户“傻瓜式”地为机器人编舞,而宇树则仍需依赖专业第三方,这在便利性上是一大进步。他已在九月预订了智元的机器,正等待到货。
众擎机器人身材高大,主打舞蹈。不过让他头疼的是“设计上不能很好折叠,必须用大箱子,无法上飞机高铁,只能开车运输。”二月下单的那台众擎,拖到十月才到货,“等到货时,热度都过去了。”价格层面,宇树因规模优势已被压得较低,而其他品牌量少成本高,处境尴尬。小雷哥曾接触一位美国客户,对方因大环境因素明确不要宇树,但其他品牌“量少、机型少、性能平平,价格反而更高”,最终订单未能达成。
与此同时,整个赛道正从早期的草莽阶段,趋向于正规化与生态化。硅基公园联合创始人郎天表示,作为全国租赁品牌最多的运营方之一,他们已提供“全包式”服务——从定制开发、动作捕捉到教学展示,一站式解决。他透露,全国拥有机器人二次开发能力的商业化公司“可能不足五十家”,更多中小租赁商会直接购买现成软件,每套价格在一千至三千元不等。在生态层面,智元机器人联合金融与研发机构发起“机器人租赁生态联盟”,构建“产品+运营+金融”的协同模式,试图通过金融杠杆和标准化运营,推动人形机器人在更多场景中实现规模化落地。浪潮起伏之后,幸存者们开始构建更深的护城河。
不过在表演过程中,人形机器人仍有很多局限。郎天表示,更多时候,是他在向客户提要求。“因为他们不了解,所以必须配合我的机器人——比如场地要平整,现场秩序要管好,甚至要根据我推荐的机型来设计环节。”比如只要涉及舞蹈表演,就必须铺地毯、拉围栏,“小朋友太容易被吸引,安全隐患必须降到最低。”天气是另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制约。今年三月,小雷哥带“笨笨”去贵州“村BA”表演,开场前突降大雨。“机器人不防水,只能临时转移到室内。”他无奈地说。这也让他思考,如果机器人真要融入人类生活,雨天无法避免,未来的设计是否应考虑基础防水?
偶尔也有顾客在得知机器人主要靠遥控操作时露出失望的表情。“其实也支持语音控制,但户外嘈杂,精度不够。遥控,目前仍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过渡形态。”小雷哥解释。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一个明显的分野正在出现:当国内的技术进步更多聚焦于“表演优化”时,国外的特斯拉Optimus、Figure AI等,正朝着“家庭化”与“通用化”的目标迈进。当前,人形机器人行业主要依赖to B业务生存,高校与科研院所是最主要的客户。to C业务中,“陪伴”远未实现,机器人更多仍以“表演卖艺”为生,租赁也就成了第二大市场。
据业内人士观察,国内除宇树凭借其在四足机器人市场的近乎垄断地位实现盈利外,多数公司仍在依赖融资维持运营。祥峰投资执行董事姜煦从资本视角分析了国内外环境的差异:相对来说,美国的资金更充足、投资方背景更多元、退出渠道更丰富,可以像OpenAI那样烧好多年等一个结果。国内和美国环境不同,机器人公司的每一轮融资都得讲出新故事、拿出订单、展示报表变化,不然不容易融到钱。她也指出了细分场景的悖论:“如果只做一个极细分的场景,采几百条数据就能做好,那这事既难赚钱,对通往‘通用’的价值也有限。但在国内,你又被迫必须展示商业化能力,这与你最终想做通用机器人的长远目标,在某些层面上是矛盾的。”
不过回到个体层面,经过近一年的起伏,小雷哥最大的体会是“祛魅”。相比国外机器人仍停留在酷炫的宣传片里,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已跑遍大街小巷,真正让人“赚到了钱”。“中国机器人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语气肯定,“而且我们不是拿来玩的,是实打实创造了商业价值。”就在他去上海登台分享租赁经验的同一天,他的机器人“笨笨”正远在一千公里之外的湖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里完成表演。十月底的一个晚上,他告诉我们,十一月的档期已经排定了三四场,还有两三场正在洽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