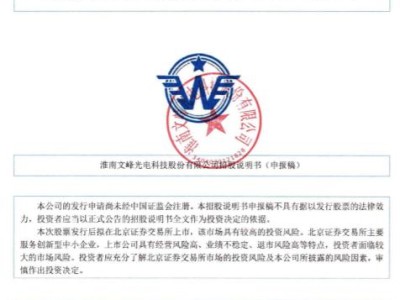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一张照片始终占据着“最震撼太空影像”的榜首。画面里,深邃的黑色宇宙背景中,一个渺小的白色身影孤独地漂浮着,没有绳索的牵绊,没有安全线的束缚,仿佛一粒被遗忘在虚空中的尘埃,静静地悬浮在地球那巨大的蓝色弧线之上。完成这一壮举的,是布鲁斯·麦坎德利斯二世,他因此成为了宇宙中第一颗“肉身卫星”。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正满怀憧憬地规划着航天飞机时代的宏伟蓝图。他们期望未来的太空任务不仅能进行观测,还能对卫星进行维修和回收。然而,这一愿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技术挑战:如何让宇航员在太空中自由移动,而非像被绳子拴住的风筝一样只能围绕飞船附近活动?
为了攻克这一难题,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装备应运而生——载人机动装置MMU。它看起来既笨重又充满未来感,宛如一把白色的“太空椅”。MMU高约1.2米,重达140公斤,背部配备了24个微型氮气喷口。宇航员只需通过扶手上的操纵杆,就能向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喷射氮气,从而在三维空间内实现自由飞行。
然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项创新被视为“自杀式”的尝试。太空中的物理法则既神秘又危险,这里没有空气阻力和摩擦力的约束。一旦MMU的某个喷口发生故障持续喷射,或者宇航员操作失误导致旋转,他们将像失控的陀螺一样在真空中无休止地翻滚,甚至径直飘向宇宙深处。没有安全绳的庇护,意味着一旦燃料耗尽或机械故障导致无法返回,航天飞机很难在短时间内变轨去“捕获”一个渺小的人体,失控就意味着成为永远漂泊的太空尸体。
尽管面临诸多反对声音,布鲁斯·麦坎德利斯二世却始终是MMU项目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他是一位兼具卓越工程师素养和资深宇航经验的专家,早在阿波罗计划时期,他就担任地面控制中心的“通讯员”,是阿波罗11号登月时阿姆斯特朗与地面通话的直接联络人。对于MMU,他有着深入骨髓的了解。从设计图纸到每一个螺丝钉,从流体力学到控制软件,他参与了这款设备研发的全过程,对每一个零件的性能和每一个可能的故障都了如指掌。
在长达10年的准备时间里,布鲁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他在模拟机上进行了成百上千小时的重复操作,预设了推进器卡死、陀螺仪故障、氧气耗尽、通讯中断等所有可能发生的恐怖场景。他训练自己在极度眩晕中保持冷静,在黑暗中盲操复位。NASA的同事们曾评价道:“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独自飞到太空深处,然后再活着飞回来,那这个人一定只能是布鲁斯。”
1984年2月3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巨大的轰鸣声划破长空。布鲁斯·麦坎德利斯二世搭乘“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冲入云霄,开启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太空之旅。而他要完成的,却是前无古人的“无绳行走”。
8分32秒后,“挑战者号”顺利抵达约300公里高度的预定轨道,以每秒7.8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绕地飞行。四天后,2月7日,历史性的时刻来临。气闸舱的门缓缓打开,布鲁斯背着巨大的白色MMU,像一个背着壳的蜗牛,缓缓飘入真空。他的面前,是深不见底的黑色宇宙;他的身后,是高速掠过地球表面的航天飞机。
他仔细检查了所有仪表,深吸一口气,然后做出了一个让地面控制中心所有人心跳骤停的动作:他解开了那根维系生命的系绳。随着手指轻轻拨动控制杆,MMU后背喷出无形的氮气流,布鲁斯开始缓缓远离“挑战者号”。他离飞船越来越远,最终达到了约98米的距离,创下了至今为止人类与载人飞船之间的最大距离纪录。
在这个距离上,“挑战者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玩具模型,而布鲁斯周围是绝对的寂静和空旷。他在太空中悬浮了近6个小时,其中有30分钟是完全脱离飞船的自由飞行。后来在回忆录中,布鲁斯描述了那种震撼灵魂的体验。他说,当他独自一人漂浮在寂静的虚空中,低头俯瞰那颗蓝色的星球时,一种被称为“总观效应”的感觉击中了他。“那里没有国界,没有战争的硝烟,没有种族的对立,也没有颜色的纷争,只有一颗美丽、脆弱、鲜活的蓝色星球,在黑色的天鹅绒背景下缓缓转动。”那一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渺小,也感到前所未有的伟大。正如他在无线电里那句发自肺腑的感叹:“我从未感到如此独立。”
在完成了预定的测试动作后,最关键的返航时刻到来了。在没有阻力的太空中,减速和刹车比加速更难。如果速度控制不好,他可能会撞毁在航天飞机上,或者擦肩而过飞向深渊。布鲁斯凭借着千万次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精准地操控着氮气喷射的频率和方向。他调整姿态,缓缓转身,对准了气闸舱。随着最后一段氮气喷出,他稳稳地停在了机械臂的抓取范围内,成功与飞船对接。那张由他的队友从驾驶舱拍摄的照片:一个渺小的宇航员,孤独地悬浮在巨大的地球之上,迅速登上了《时代周刊》等全球各大媒体的封面,成为了航天时代的精神图腾。
虽然MMU装置后来因为安全风险过高而被NASA永久退役,被更安全的机械臂和系绳系统所取代,但这并没有削弱布鲁斯壮举的光芒。那张照片反而变得更加珍贵和绝版,因为它定格了人类探索史上一个不可复制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