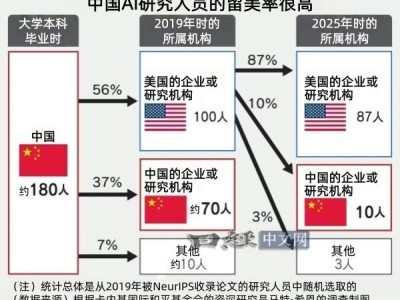浩瀚宇宙中,总有一群人执着于探索星空的奥秘。他们或翻山越岭寻找天文台址,或穿越极地拍摄星轨,或搭建监测网守护太空安全。这些追星人用各自的方式,将人类的好奇心投向无垠的深空。
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角,海拔4500米的赛什腾山上,银白色的天文圆顶正在密集排列。这座曾因石油枯竭而沉寂的小镇冷湖,如今因纯净的暗夜星空重获新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邓李才带领团队,在这里完成了亚洲最大光学天文观测基地的选址工作。
2017年,邓李才为"恒星观测网络计划"寻找新家时,遇到了同样在寻找发展机遇的地方干部田才让。当田才让拿着红头文件找到这位满身尘土的天文学家时,两人一拍即合。但选址过程充满艰辛,赛什腾山陡峭碎石遍布,团队成员杨帆每次登顶都要靠一瓶可乐奖励自己。
"山上根本没有路,有次我差点踩空坠崖。"邓李才回忆道。他们用直升机吊装设备,在山顶完成基建。当视宁度测量仪传来0.79角秒的数据时,整个团队沸腾了——这个数值达到世界一流水平。2021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正式确认冷湖赛什腾山为国际顶级光学天文台址。
常年往返高原的邓李才,曾因血压升高需要服药控制。但他通过坚持跑步、健走和严格控制体重,最终成功停药。"没有好的体能基础,冷湖选址根本做不下来。"如今60多岁的他依然能在海拔4000米的山上健步如飞。
在遥远的阿尔卑斯山脉,北京大学博士生王凯翔正经历着双重冒险。2023年UTMB环勃朗峰越野赛中,他在强风中完成滑雪挑战;同年,他以独立第一作者身份在《自然》发表论文,揭示了超致密矮星系的演化机制。这位同时热爱极限运动和星空摄影的年轻人,将科研与爱好完美融合。
"科研常要靠天吃饭,这种不确定性与星空摄影很契合。"王凯翔说。2024年5月,他通过空间天气预报提前锁定北京金山岭长城,成功拍摄到极光。当红色光柱出现在长城背后的天际时,他忍不住落泪:"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北京境内的长城上拍到极光。"
在内蒙古长大的刘博洋,从小就对星空充满好奇。父母送的入门望远镜让他第一次看清月球环形山,高中加入天文社后,他更是一头扎进星空的世界。2012年成为知乎答主后,他经常花数小时查阅前沿资料,为网友解答"脑洞大开"的天文问题。
读博期间陷入迷茫时,导师的话点醒了他:"你可以不做科研,但如果不做科普,一定是科普界的损失。"2019年,他发现一个传播伪科学的邪说团体,通过专业科普文章逐一反驳其编造的概念,最终迫使多个伪科学账号停止运营。
"科普不只是讲知识,还能'救人'。"刘博洋说。2022年,他成功记录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全部12种构型。2023年,在知乎"灯塔计划"支持下,他将跟踪空间站的技术发展成全国监测网,给太空装上"监控系统"。
这套被内部称为"天罗地网"的系统,通过在不同地点建立观测点,实时记录卫星位置和轨迹。2024年某卫星发射异常时,团队在5小时内获取关键影像,为救援工作提供重要支持。刘博洋希望,这些鲜活的科普素材能让更多人理解太空安全的重要性。
从冷湖的荒山到阿尔卑斯的雪峰,从知乎的科普文章到太空的监测网络,这些追星人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对星空的热爱。当望远镜圆顶在暮色中次第打开,当滑雪板划过冰川的轨迹与星轨重叠,当监测网捕捉到卫星的每一次移动,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从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