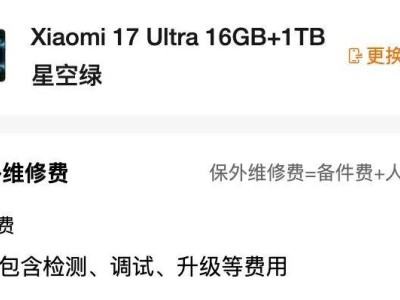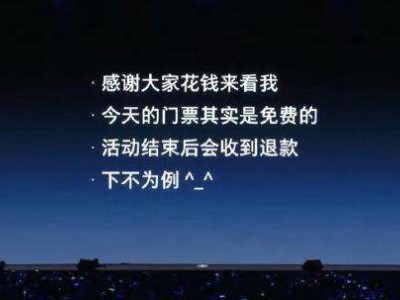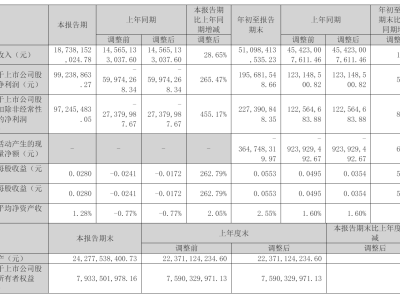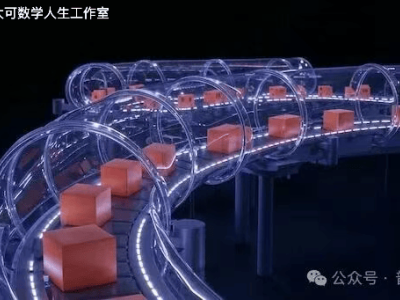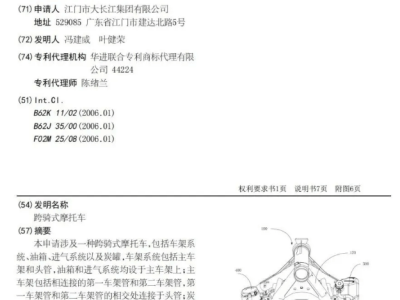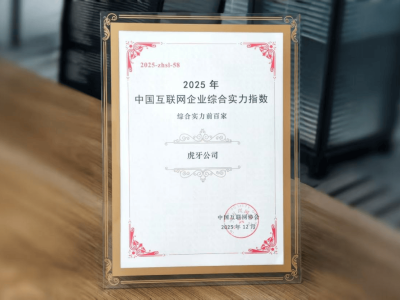巴菲特在近期发布的公开信中宣布将“安静辞职”,这位95岁的投资大师在信中不仅分享了对市场波动的见解,更以朴素的语言探讨了人生价值的本质。他强调,真正的伟大不在于财富积累或社会地位,而在于善行与人性尊严的平等——无论是清洁工还是企业领袖,都应获得同等的尊重。这一观点引发了对现代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深度思考。
核心矛盾聚焦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自我衡量方式:内在标尺与外在标尺。前者以个人价值观为基准,强调自我认同与内心满足;后者则依赖外界评价,将社会比较作为行为导向。巴菲特指出,过度依赖外在标准会导致行为扭曲,人们可能陷入迎合他人期待的陷阱,而非追求真正有意义的目标。这种失衡在财富领域尤为显著,当金钱成为衡量成功的唯一尺度时,个体往往失去对生活本质的感知。
19世纪美国石油大亨保罗·盖蒂的案例极具警示意义。作为首位身价超10亿美元的富豪,他在豪华城堡中接受采访时却坦言:“我嫉妒那些性格更好的人。”这种精神空虚源于他将财富视为自我价值的全部,却无法建立内在认同感。类似困境在“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家族身上演变为家族悲剧:3000亿美元遗产在三代人手中挥霍殆尽,继承人雷金纳德沉迷酒精赌博,45岁死于肝硬化;乔治建造的12542平米庄园因维护成本过高导致破产,最终沦为旅游景点。家族成员陷入无休止的物质攀比,却无人能按本心生活。
这种异化现象在当代社会依然普遍存在。NBA球星安托万·沃克12年职业生涯赚取1.08亿美元,却因无节制消费和承担30位亲友开销而破产。值得关注的是,他在破产后通过多年工作偿还1270万美元债务,这段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真正摧毁我的不是奢侈消费,而是‘必须照顾所有人’的虚荣心。”这印证了心理学中的“过度责任”陷阱——当金钱成为维系人际关系的工具时,个体将陷入永无止境的付出循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建立内在价值体系的人群。畅销书作家摩根·豪泽尔在《金钱的艺术》中描述,他与妻子通过储蓄获得财务独立后,将时间投入徒步、园艺、阅读等持续带来愉悦的活动,这种生活方式不受收入波动影响。奈飞联合创始人马克·伦道夫更将“与发妻白头偕老”和“保持亲子理解”列为人生最大成就,远超过商业成功。这些案例揭示,当金钱回归工具属性时,才能真正服务于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
临终关怀牧师的观察提供了更具普世性的视角。在为数千名患者提供精神慰藉的过程中,他发现关系紧张的家庭中,子女常感谢父母提供的物质支持;而亲密家庭的孩子则会说:“谢谢你相信我。”这种无条件的信任构建了孩子的核心自我价值,使其无需通过外界认可证明自身存在。正如巴菲特所言:“衡量人生成功的终极标准,是爱你的人中真正爱你的数量。爱无法购买,只能通过成为值得被爱的人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