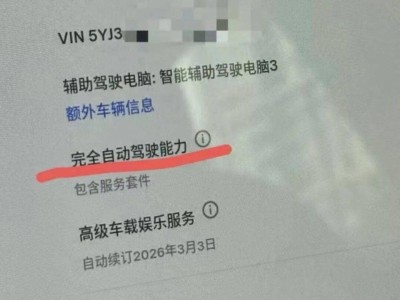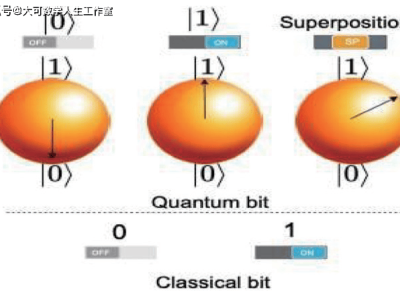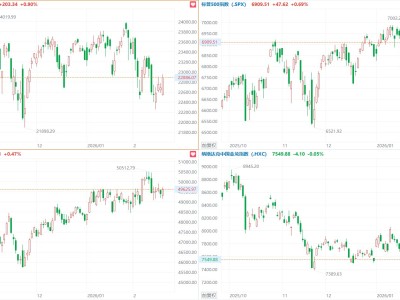作者:时春香
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迁徙”,只因心向一处。
每年的这个时候,十几亿人,往同一个方向走。
过去几年,我们透过各位笔下的文字,看到了归途的思绪、重逢的悲欢、故里的新颜……
这些看似再平凡不过的日常,因为被写下来,所以有了重量。
格隆汇《归乡记》系列,今年还在。
不为别的,只是觉得:普通人的归乡与奔赴,值得被认真记录。
这是本系列第十五篇。
01
南京的腊月总是湿冷入骨。那种冷不是北方大刀阔斧的砍杀,而是像细密的针,顺着袖口领口往骨头缝里钻。
我把最后一件羽绒服塞进那个二十八寸的行李箱,拉链咬合的声音在空荡的客厅里显得有些刺耳。囡囡蹲在一旁,手里摆弄着我的围巾,把流苏编成歪歪扭扭的麻花辫。她抬起头,那双眼睛清亮得像两丸黑水银。
“妈妈,外婆家的山上有老虎吗?”囡囡操着一口软糯的南京话问我。
我笑了,把围巾从她手里解救出来,给她理了理乱糟糟的刘海。
“没有老虎,但是有金丝猴,尾巴这么长,在树上飞来飞去。”
囡囡“哇”了一声,又问:“那外婆凶吗?”
我手上的动作停住了。凶吗?记忆里的母亲是个急性子,说话嗓门大,做事风风火火,但在我的印象里,她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对我凶过。只是这一次,事情有点不对劲。
半个月前,母亲打来电话,语气慌张得让我心惊肉跳。
“幺儿,那坛酸汤坏了。”
我当时正在改稿子,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随口应道:“坏了就倒了嘛,重新起一坛就是了。”
“你不晓得!”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甚至带了一丝哭腔,“这是那坛老汤,那是你外婆传给我的引子,四十年都没坏过,咋个今年子就没得味了呢?肯定是哪里不对头,你今年过年一定要回来,帮我看看是咋回事。”
电话那头,我听见父亲在一旁小声嘀咕,喊我莫要听母亲瞎说。接着就是母亲的呵斥声,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那一刻,我心里的弦被猛地拨动了一下。
那坛酸汤是家里的定海神针。在贵州铜仁江口县那个被梵净山云雾缭绕的小城里,没有酸汤的日子是没法过的。那只粗陶坛子蹲在灶台最阴凉的角落里,像个沉默的守卫。母亲把淘米水发酵,加入西红柿、辣椒、木姜子,那股子酸爽醇厚的味道,不仅煮鱼好吃,就连我们就着汤泡冷饭,也能呼噜呼噜吃下两大碗。
四十年没坏过的老卤,怎么突然就坏了?
我看着窗外。南京的天空灰扑扑的,雨夹雪正在酝酿。我想起母亲电话里的焦虑,那种焦虑不像是因为一坛汤,倒像是因为抓不住某种正在流逝的东西。
高铁在铁轨上飞驰,像一支离弦的箭,穿透江南的水网,扎进湘西的丘陵,最后冲向贵州的万重山峦。
囡囡趴在窗户上,看着窗外的景色变化。起初是平原上整齐的田块,后来变成了连绵起伏的山包,再后来,就是巍峨耸立的大山。
“妈妈,那个洞是不是怪兽的嘴巴?”囡囡指着一个个飞速掠过的隧道问。
“那是大山的眼睛。”我告诉她。
车厢里渐渐热闹起来,乡音越来越浓。我听见后座有人用那熟悉的调子打电话,说到了凯里,马上就转车。那声音像一把钩子,把我也钩回了那个潮湿温润的地方。
江口站到了。
一下车,冷空气裹挟着大山特有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这不是南京那种阴湿的冷,而是一种清冽的、带着泥土腥气的凉。我深吸一口气,肺腑里像是被洗了一遍。
远处,梵净山的轮廓在云雾里若隐若现,像一幅没干透的水墨画。锦江河的水静静地流淌,泛着青绿色的光
02
出租车在蜿蜒的县道上跑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停在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院坝前。
院子里的柚子树比我记忆中更高大了,叶片上挂着细碎的水珠。老屋还是那栋老屋,只是墙皮有些剥落,露出了里面的红砖,像老人脸上褪不去的斑。
还没等我把行李从后备箱提下来,母亲就从堂屋里冲了出来。
她老了。这是我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
两年前见她时,她的腰板还挺得直直的,头发虽然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可现在,她的背有些佝偻,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显得身形更加瘦小。父亲跟在后面,手里拿着旱烟杆,冲我憨厚地笑,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外婆!”囡囡躲在我的腿后,探出半个脑袋,怯生生地喊了一句。
“哎哟,我的乖孙孙!”母亲那张满是皱纹的脸瞬间舒展开来,像一朵干枯的菊花遇水绽放。她想伸手去抱囡囡,又在围裙上使劲擦了擦手,似乎怕弄脏了囡囡那件粉白色的羽绒服。
进屋。父亲接过我手里的箱子,沉甸甸的,压得他身子一歪。我心里一酸,赶紧伸手托了一把。
屋里光线有些暗,火塘里的炭火偶尔发出“毕剥”的声响,衬得屋里格外静谧。空气里弥漫着熏腊肉的烟火味和一股淡淡的霉味。悬在梁上的腊肉黑乎乎的,像一块块坚硬的石头。
囡囡指着那些腊肉问:“妈妈,那是硬邦邦的黑石头吗?”
我笑着解释:“那是好吃的肉肉。”
母亲没顾得上寒暄,也没顾得上给囡囡拿零食,她拉着我的手,径直往厨房走。她的手粗糙干硬,掌心里全是老茧,划得我手背生疼。
“快来看看,快来看看。”母亲嘴里念叨着,急切地把我带到那个角落。
那个熟悉的粗陶坛子依然蹲在那里,坛沿的水封干了一半。母亲揭开盖子,一股熟悉的酸香气扑鼻而来。这味道冲进鼻腔,瞬间激活了我所有的味蕾。
“这不是好好的吗?”我疑惑地问。
母亲摇摇头,眉头紧锁成一个川字。
“没味了。前几天我舀了一碗煮鱼,你爸爸说淡得很,一点酸味都没得。我又加了盐,加了酒,还是不得行。你尝尝,是不是坏了?”
我拿过一双筷子,伸进坛子里蘸了一点红亮的汤汁,放进嘴里。
酸。
很纯正的酸,带着米汤发酵后的回甘,还有木姜子特有的清香。这分明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一点都没变。
“妈,没坏啊。”我放下筷子,认真地说,“好酸的,味道正得很。”
母亲狐疑地看着我:“真的?莫不是你也在哄我?”
“真的。”我加重了语气,“比珍珠还真。”
母亲还是不信,她颤颤巍巍地拿起筷子,自己蘸了一点放进嘴里,吧唧了几下嘴,脸上露出一片茫然。
“咋个我吃起还是像白开水一样?是不是引子死了?”
她站在那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手足无措。那坛汤是她迎接女儿回家的最高礼遇,如果汤坏了,她似乎就失去了爱我的资格。
这时候,父亲走了进来。他看了一眼母亲,又看了看我,那是眼神的示意。
“老婆子,你去割一块腊肉下来,晚上给囡囡煮起吃。”父亲支开了母亲。
母亲“哦”了一声,转身出去了,步履有些蹒跚。
等母亲走远了,父亲才叹了一口气,坐在小板凳上,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
“其实那坛汤没坏。”父亲压低了声音,像是在说一个秘密。
“那是咋回事?”我蹲在父亲面前,心里隐隐有了不好的预感。
“是你妈的嘴巴坏了。”父亲指了指自己的舌头,“去年子生了一场病,发高烧,烧退了以后,味觉就不灵了。吃啥子都没得味,咸的淡的酸的辣的,她都分不清楚。”
我愣住了。
“她不信是自己老了,非说是汤坏了。”父亲苦笑了一下,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样,“她怕做不出以前那个味道,怕你回来吃不惯,就不想回来了。她在电话里跟你急,是心里头急啊。”
我感觉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闷得发慌。
原来,那个电话里的焦虑,不是因为一坛汤,而是因为一个母亲对子女逐渐疏离的恐慌。她怕失去了“味道”这个纽带,她在这个家里,就真的成了一个无用的人。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听见厨房里有动静,便披衣起床。透过门缝,我看见母亲正对着那口大铁锅发呆。
锅里煮着面条,热气腾腾。她拿起勺子尝了一口汤,眉头紧锁,似乎在努力捕捉那一丝逃逸的味道。过了一会儿,她摇摇头,又往锅里加了一勺盐,再尝,依旧是一脸茫然。
她站在晨光里,手里举着勺子,像个失去了罗盘的水手,在那片熟悉的味觉海洋里迷了路。
我背过身去,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03
除夕夜,大山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震得窗纸嗡嗡作响。
堂屋的桌子上摆满了菜。腊肉炒折耳根、血豆腐、米豆腐,还有那一锅热气腾腾的酸汤鱼。
鱼是从锦江河里打上来的黄辣丁,肉质细嫩。红亮的汤汁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每一声响动都像是把沉睡的食欲唤醒。
母亲坐在桌边,神情有些紧张,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指关节都搓红了。她不敢动筷子,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夹起一块鱼肉,蘸了满满的汤汁,放进嘴里。
“好吃!”我夸张地大喊一声,“妈,这个味道绝了!我在南京想这一口想了一年了,做梦都在流口水。”
母亲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像风吹开了灰烬,露出了里面的火星。
“真的?”
“真的!不信你问囡囡。”我给囡囡盛了一小碗汤。
囡囡从小在南京长大,吃得清淡,我其实有点担心她吃不惯这又酸又辣的东西。
囡囡端起碗,小小地抿了一口。她的眉毛瞬间皱了起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小嘴巴不停地吸着气。
“好辣!”囡囡吐着舌头。
母亲的眼神又黯淡下去。
“但是……”囡囡吧唧了一下嘴,似乎在回味,又伸出小舌头舔了舔嘴唇,“酸酸的,像吃柠檬糖一样。妈妈,我还要喝!”
囡囡把碗递过来,脸上带着那种发现了新大陆的兴奋。
“还要得!还要得!”母亲高兴得手都在抖,连忙接过碗,给囡囡又舀了满满一大勺,“吃这个开胃,多吃点,长高高。”
那一顿饭,母亲吃得格外香。虽然我知道,在她的嘴里,那或许依然是一碗没有什么味道的白开水,但在她的心里,那一定是世界上最美的滋味。
我看着她在热气里模糊的脸,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间的味道,其实并不完全依赖味蕾。有一种味道,是刻在血脉里的,是只要一家人坐在一起,就能品尝到的甘甜。
这坛酸汤,封存的不是西红柿和辣椒,而是母亲想留住我的那份执念。
初五一早,我们要走了。
后备箱被塞得满满当当,自家做的腊肠、山上采的干蘑菇、还有那一瓶用矿泉水瓶装好的酸汤引子。
“拿回去,自己起一坛。想吃的时候就弄。”母亲隔着车窗嘱咐我,眼圈红红的。
“妈,明年我还回来。”我握住她满是老茧的手。
“好,好,回来就好。”母亲不住地点头。
车子发动了,缓缓驶出院坝。
我从后视镜里往外看。父母并肩站在路口,身后的老屋在晨雾里静默无言。风吹动母亲那件暗红色的棉袄,像是一团在风中瑟缩的火苗。
随着车子越开越远,他们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了两个黑点,融入了身后那座巍峨的大山之中。
“妈妈,外婆家的汤真好喝。”囡囡坐在安全座椅上,怀里紧紧抱着那个装酸汤引子的矿泉水瓶,像抱着个宝贝。
“是啊,好喝。”我轻声说,伸手摸了摸那个瓶子。瓶身还带着体温。
车子拐过一个弯,锦江河的水依旧静静流淌。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这坛酸汤的味道,都会像这河水一样,在我的生命里长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