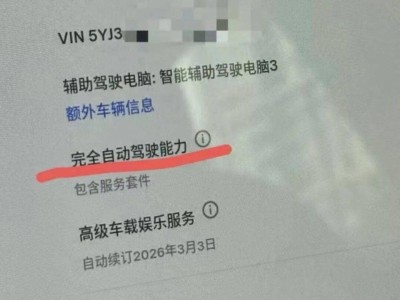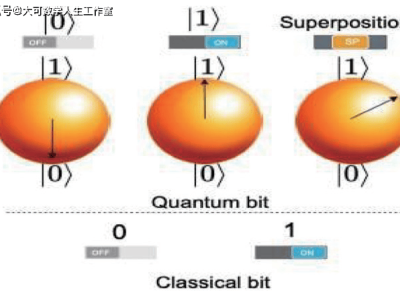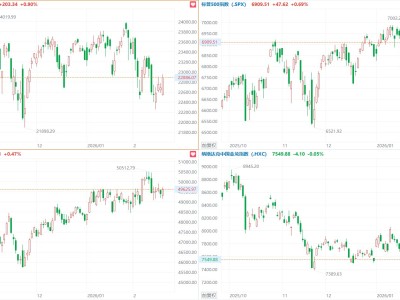作者:黄革丽
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迁徙”,只因心向一处。
每年的这个时候,十几亿人,往同一个方向走。
过去几年,我们透过各位笔下的文字,看到了归途的思绪、重逢的悲欢、故里的新颜……
这些看似再平凡不过的日常,因为被写下来,所以有了重量。
格隆汇《归乡记》系列,今年还在。
不为别的,只是觉得:普通人的归乡与奔赴,值得被认真记录。
这是本系列第十四篇。
01
腊月二十七,上海虹桥站。
我拖着行李箱穿过人群,像一条逆流而上的鱼。到处都是人,背着蛇皮袋的、拎着礼盒的、抱着孩子的,每个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涌——检票口。广播里一遍遍播报车次信息,女声温柔而机械,淹没在嘈杂的人声中。
我的车次是G1472,终点站是安徽六安。四个半小时,这是我今年回家的距离。
候车室里,对面坐着一对年轻夫妻,女的怀里抱着个婴儿,男的脚边放着两个大编织袋,用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婴儿醒了,开始哭,女的撩起衣服喂奶,动作自然得像在家里。男的低头看手机,屏幕上是某个工厂的车间照片,他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收起来,扭头看窗外。
窗外是铁轨,一列动车正缓缓进站。
我想起十年前,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那时候从六安到上海,要坐一夜的绿皮车,硬座,没空调,窗户能打开。我靠窗坐了一夜,看着外面的田野慢慢变成城市,又慢慢变回田野。凌晨三点的时候,车厢里有人开始吃泡面,香味飘过来,我饿了,但没舍得买——五块钱一桶,太贵了。
后来我常跟人说起那一夜,说起那个凌晨三点的泡面味。那是我对上海的第一印象,不是外滩的繁华,不是南京路的人潮,而是一桶红烧牛肉面的味道。
十年过去了,我还在上海。从工厂流水线做到房产中介,又从房产中介做到现在这家公司,做的是电商运营。工资涨了,职位变了,但每年这个时候,我还是得买一张回家的票,挤上火车,穿过几百公里,回到那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县城。
检票了。我跟着人群往前走,走过天桥,下到站台。动车安静地停在那里,流线型的车头,雪白的车身,跟十年前那辆绿皮车是两个世界的产物。
我找到座位,靠窗。放好行李,坐下来,看着窗外的站台。有人在抽烟,有人在拍照,有人在打电话:“妈,我上车了,下午三点到,不用接,我自己回去。”
动车启动,慢慢加速,把站台甩在身后。然后是城市,高楼、立交桥、密密麻麻的小区。再然后是郊区,工厂、仓库、大片大片的荒地。最后是田野,冬天的大地裸露着,麦苗刚冒出头,矮矮的、绿绿的,贴着地皮。
我靠着窗户,睡着了。
02
醒来的时候,车已经过了合肥。
窗外的风景变了,山多了起来,一座连着一座。隧道也多,刚出这个又进那个,光暗交替,晃得人眼晕。我揉了揉眼睛,看看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车厢里安静下来,大部分人都在睡觉。对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戴着眼镜,面前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正在看什么文件。他偶尔抬起头,揉揉眉心,然后继续看。他穿得很整齐,西装、衬衫、皮鞋,但袖口有点脏,像是蹭到了什么。
我猜他也是回六安的,也许是哪个单位的干部,也许是做生意的。我没问,他也没说。
快到站的时候,列车员过来提醒:“六安站到了,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
我站起来,拿下行李箱,往车门走。门开了,冷风灌进来,比上海冷多了。我缩了缩脖子,走下火车。
站台上全是人,接站的、下车的、问路的,乱成一团。我拖着行李箱往外走,路过一个小卖部,里面卖着六安瓜片、霍山石斛、还有各种当地特产。老板坐在门口晒太阳,眯着眼,手里捧个保温杯。
出了站,我给父亲打电话:“爸,我到了。”
“我在出站口右边,那棵大树底下。”
我拖着箱子往右边走,远远就看见了那棵大树。树底下停着一辆摩托车,父亲跨在上面,一条腿支着地,正往这边张望。
他老了。这是我第一眼看见他时的感觉。
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更深了,穿一件旧棉袄,袖口磨得发白。他看见我,冲我挥手,脸上露出笑。我走过去,他把摩托车的后备箱打开,让我把行李箱放进去。
“上来吧。”他说。
我坐上后座,抓住他棉袄的两侧。摩托车发动,突突突地往前开。
这条路我太熟悉了。从县城到我们镇,十八公里,骑摩托车要四十分钟。小时候父亲带我去县城,就是走这条路。那时候是土路,坑坑洼洼,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后来修了柏油路,又扩宽了一次,现在两边还装了路灯。
父亲骑得不快,四五十码的样子。风吹过来,把他的棉袄吹得鼓起来,我抓得更紧了些。
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他放慢速度,扭头跟我说:“这是你大舅家那个村,你记得不?”
我往那边看,一排排两层小楼,白墙红瓦,整齐得像规划过。我记得小时候来这儿,全是土坯房,矮矮的,黑黑的,下雨还漏。
“都盖新房了。”我说。
“嗯,新农村建设,统一盖的。你大舅家也盖了,去年搬进去的。”
摩托车继续往前开。路过一片麦田的时候,他又说:“这块地是你二叔的,今年种的是小麦,长得还行。”
我看着那片麦田,绿油油的,在冬天的阳光下泛着光。麦田尽头是一排杨树,光秃秃的,枝丫直戳向天空。
03
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
母亲站在门口等,穿着围裙,手上沾着面粉。看见我从摩托车上下来,她快步走过来,想抱我又没抱,只是拍了我胳膊一下:“瘦了,上海吃不饱啊?”
“没有,瘦点好,健康。”
她瞪我一眼:“健康什么健康,脸上都没肉了。快进屋,外面冷。”
屋里烧着炉子,暖烘烘的。炉子上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母亲让我坐沙发上,自己去厨房接着忙。父亲把摩托车推进院子里,又把我的行李箱拎进来,然后坐在炉子边抽烟。
“今年怎么样?”他问。
“还行,跟去年差不多。”
“工资涨了没?”
“涨了一点。”
他点点头,没再问。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妈天天念叨你,说你在外面吃不好,睡不好,太累了。”
我看着厨房的方向,母亲正在炒菜,锅铲翻飞,油烟升腾。她背对着我,但我能看见她的动作,利落又熟练,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晚饭很丰盛,一桌子菜,大部分是我爱吃的。红烧肉、糖醋排骨、清炒时蔬、还有一个砂锅炖的鸡汤。母亲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夹得冒尖儿。
“多吃点,多吃点,这个排骨是我专门去镇上买的,你爸说你爱吃。”
父亲不说话,埋头吃饭。但他偶尔抬起头,看我一眼,然后继续吃。
吃完饭,我帮着收拾碗筷。母亲不让,让我坐着看电视。电视里在放什么春晚彩排的新闻,一群人穿着花里胡哨的衣服在台上跳。
我坐了一会儿,觉得无聊,站起来在屋里转。墙上还挂着那张全家福,是我考上大学那年拍的,十年了。那时候父亲头发还是黑的,母亲也没这么瘦,我站在中间,笑得傻乎乎的。
旁边是一张奖状,我小学三年级得的,三好学生。纸已经发黄了,边角有点卷,但还贴在那里。
我忽然想起,这个房子也是二十多年前盖的了。那时候我刚上小学,父亲借了钱,请了人,一点一点盖起来的。盖好那天,他站在院子里看,看了很久,然后说:“这辈子就住这儿了。”
他真的就住这儿了。二十多年,哪儿也没去。
04
第二天是大年二十八,父亲说要带我去镇上办年货。
早上八点,我们骑着摩托车出发。我坐在后座,抱着一个空编织袋,准备用来装东西。
镇子不大,一条主街贯穿南北,两边是各种店铺。快到年了,街上人很多,摩肩接踵的。父亲把摩托车停在熟人门口,我们开始逛。
先去了菜市场。人声鼎沸,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父亲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他走到一个肉摊前,跟老板讨价还价,最后买了十斤猪肉、五斤排骨。
“今年的肉便宜了,”他说,“比去年便宜好几块。”
然后又去买鱼。卖鱼的是个年轻人,戴着胶皮手套,手冻得通红。他捞起一条草鱼,问:“这条行不?”
父亲看了看:“太大了,换条小的。”
年轻人换了一条,父亲还是嫌大。换了好几次,最后挑了一条两斤左右的。
“就这条吧。”
年轻人把鱼往地上一摔,鱼蹦了两下,不动了。然后刮鳞、开膛、掏内脏,动作麻利得很。
买完鱼,又去买菜。青菜、萝卜、蒜苗、芹菜,一样买一点。编织袋越来越沉,我换了个肩膀背着。
路过一个卖春联的摊子,父亲停下来,一张一张地看。卖春联的是个老头,戴老花镜,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捧个保温杯。
“这个咋样?”父亲指着一副问我。
我看了看,上面写着“家和万事兴”,挺俗的,但没什么不好。
“行。”
他掏出钱,买了。老头把春联卷起来,用根红绳系好,递给他。
往回走的时候,路过一个电器店,门口摆着几台电视机,正在放什么节目。几个老头围在那儿看,一边看一边议论。父亲也停下来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
“家里的电视也老了,”他说,“该换了。”
我没接话。我知道他舍不得换,那台电视买了快十年了,还能看,他就一直用着。
05
大年三十那天,按照老家的规矩,要上坟。
下午两点,我跟父亲带着纸钱和鞭炮,往后山走。后山不高,走二十分钟就到了。上面埋着爷爷、奶奶,还有太爷爷太奶奶。
爷爷走的那年我上初中,记得他躺在棺材里的样子,穿一身新衣裳,脸色蜡黄,像睡着了。奶奶走得更早,我上小学的时候,她就不在了。
父亲跪下烧纸,我也跟着跪下。火苗舔着纸钱,把它们变成灰烬。灰烬飘起来,落在我们的头发上。
“爷爷年轻的时候,是生产队的队长,”父亲忽然开口,“那时候干活挣工分,他一个人顶两个人。你奶奶说他太实在,不知道偷懒。”
我没说话,听着。
“后来分田到户,他就种地,一直种到动不了。走的那年,还在地里干活呢,突然就倒下了。”
火快灭了,父亲又添了一把纸。火重新燃起来,映得他的脸红红的。
“他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
烧完纸,父亲站起来,对着坟头鞠了三个躬。我也跟着鞠。
往回走的路上,父亲走得很慢。他看着远处的山,说:“等我以后也埋这儿,你记得常来看看。”
我心里一紧,不知道说什么。
他扭头看我一眼,笑了:“怕什么,人都有这一天。”
06
除夕夜,一家人围在一起看春晚。
父亲坐在沙发上,没看一会儿就睡着了。母亲推他:“醒醒,待会儿该放相声了。”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看了一眼,又闭上了。
我坐在旁边刷手机,朋友圈里都是年夜饭的照片。母亲端着饺子从厨房出来,热气腾腾的。
“快趁热吃,韭菜鸡蛋馅的。”
我夹起一个,咬一口,烫得直吸气。母亲笑了:“慢点吃,没人抢。”
电视里开始倒计时,十、九、八、七……父亲被吵醒了,揉揉眼睛,看着电视。母亲站起来,走到窗边,说外面开始放烟花了。
我也走过去,拉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带着硝烟的味道。远处有人在放礼花,一朵一朵在夜空中炸开,照亮了半个天空。近处也有人放,噼里啪啦响成一片。
零点的钟声响起来,父亲点了一挂鞭炮,在院子里噼里啪啦响。母亲站在门口捂着耳朵看,脸上带着笑。
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这就是过年。
不是那些复杂的仪式,不是那些热闹的场面,就是这一刻,一家人在一起,听着鞭炮声,闻着硝烟味,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07
初五那天,我该走了。
早上起来,母亲已经把早饭做好了。小米粥、咸菜、油饼,摆了一桌子。她坐在旁边看着我吃,不停地让我多吃点。
“路上慢点,到了打电话。”
“嗯。”
“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她老了,真的老了。
“五一吧,五一我回来。”
她点点头,没再问。
吃完饭,我去院子里拿行李。父亲已经把摩托车推出来了,后座上绑着我的行李箱。
“走吧,我送你去车站。”
我坐上后座,抓住他的棉袄。摩托车发动,突突突地往前开。
路上没什么人,都在家过年呢。风吹过来,冷冷的。我看着父亲的背影,他腰板挺直,目视前方,骑得很稳。
到了车站,他停下来,帮我把行李箱拿下来。
“进去吧,别误了车。”
“爸,你回吧,路上慢点。”
他点点头,跨上摩托车,发动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骑着摩托车,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路的尽头。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他就是这样骑着摩托车,带我去镇上、去县城、去所有我想去的地方。他的后座,是我整个童年。
现在,我长大了,要自己去远方了。而他,还骑着那辆摩托车,在那个小镇上,等着我回来。
我转过身,走进车站。
08
动车启动,往东开。
我看着窗外,田野、村庄、山峦,一一掠过。那个叫家乡的地方,正在被一点点甩在身后。
但我心里知道,无论走多远,那个地方永远在那里。那里有我的父亲母亲,有那辆老摩托车,有那条通往镇上的路。
那里是我出发的原点,也是每一次跋涉的终点。
愿所有的奔波过后,依然拥有可以回去的地方。
我的故乡,在大别山脚下,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镇边上。它没有繁华,没有热闹,只有一辆摩托车,一个父亲,和一个永远等着我回去的后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