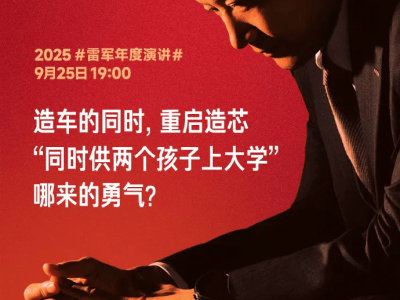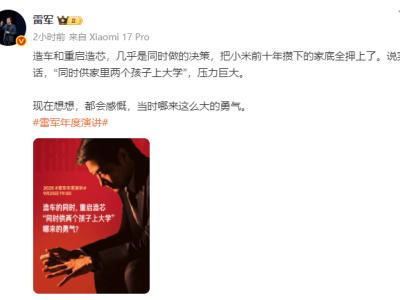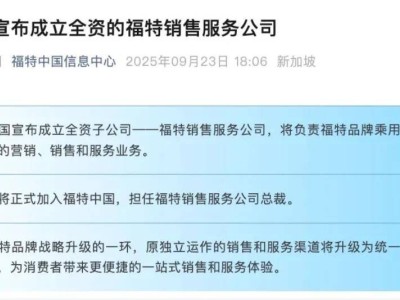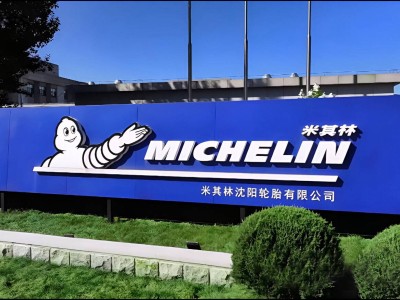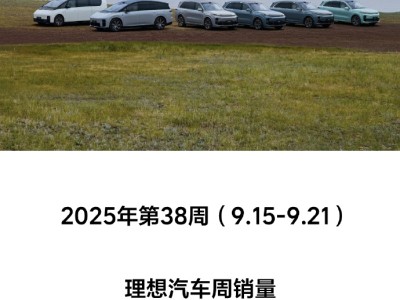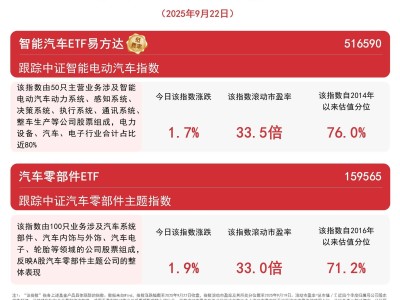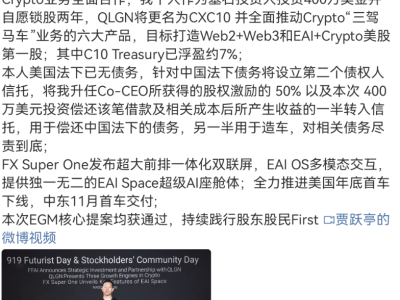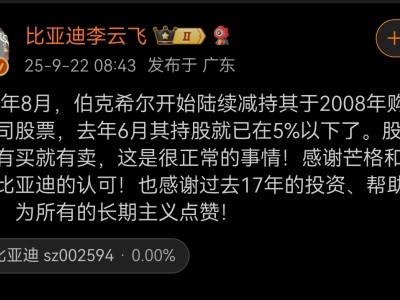当你在B站、小红书或抖音上滑动屏幕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两位嘉宾端坐在麦克风前,展开一场长达数小时的深度对话。从陈鲁豫与窦文涛的思维碰撞,到罗永浩与李想的行业探讨,这些看似传统访谈的内容,正以“视频播客”的新形态席卷中文互联网。
视频播客并非横空出世的概念。在YouTube生态中,从个人创作者到专业对谈节目,音频内容同步录制视频版本早已成为常态。这种“可听可看”的模式,为订阅者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而今年,随着B站、小红书、抖音等平台的集体发力,视频播客在中国内容市场引发了新一轮讨论热潮。罗永浩、陈鲁豫等名人推出的视频播客,单期播放量突破百万,被业界视为“播客商业化破局的关键信号”。
播客的起源可追溯至2001年苹果iPod的发布。这款便携式音频设备颠覆了传统广播的收听方式,让“随时随地的音频内容”成为可能。2007年iPhone的诞生,进一步将播客从网页端迁移至移动端。然而,在中文互联网世界,播客长期处于小众状态。直到2020年聚合平台“小宇宙”上线,这一概念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
据eMarketer数据,中国现有1.5亿播客听众,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这群用户呈现出独特的“三高”特征:高学历、高黏性、高消费潜力。CPA中文播客的调研显示,49%的听众来自一线城市,29.8%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均每周收听时长达4.1小时。但矛盾的是,这个看似优质的受众群体,却长期困扰着播客的商业化进程。
独立播客主林安从2019年开始制作《逆行人生》,她坦言:“最初做播客纯粹出于兴趣,完全没考虑过赚钱。”这种心态在创作者中颇为普遍。CPA的调研也印证了这一点:播客主的首要创作动机是“链接更多人”,其次是“扩大个人影响力”。在变现模式上,广告成为主要选择,但多数创作者一年仅能接到一两次广告合作。
与中文市场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播客行业早已形成成熟的商业生态。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播客广告市场规模达4.79亿美元。在加拿大生活的Daria Cathleen观察到:“播客就像日常生活中的背景音,尤其在通勤场景中不可或缺。”这种需求差异,部分解释了中美市场的分化——中国除一线城市外,长距离通勤场景较少,限制了播客的普及基础。
广告公司媒介Liz指出,播客商业化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创作者对广告类型极为挑剔,担心破坏节目调性,常拒绝外卖券等“接地气”的广告;另一方面,品牌方对播客的认知仍停留在“可选渠道”阶段,多数投放源于部门预算分配或工作亮点需求,而非真正的战略布局。这种双向筛选导致广告资源集中于奢侈品、个护等需要品牌建设的领域,本土品牌则因追求即时ROI而望而却步。
视频播客的兴起,为行业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从海外经验看,视频形态能更直观地展示品牌信息,通过切片传播延长内容生命周期,提升商业合作效率。例如,JustPod公布的制作流程显示,视频播客需要专人负责嘉宾沟通、场景布置、现场把控及物料审核,制作成本显著高于纯音频内容。这种升级也引发了争议:独立创作者林安认为,视频播客更像“主打音频的视频节目”,而非播客的自然延伸。
听众的态度同样分化。一位小红书用户直言:“听播客就是为了解放双手,如果还要看画面,和普通视频有什么区别?”出镜顾虑也成为独立创作者的障碍。Liz接触的播客主中,不少人因社恐或外形因素拒绝视频化。这种矛盾折射出视频播客的本质:它既是内容形式的升级,也是创作门槛的抬高。
对比美国市场,企业家播客的繁荣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在硅谷,播客成为企业高管与公众对话的新渠道。挪威主权财富基金CEO Nicolai Tangen等商业领袖亲自下场制作内容,通过价值观输出替代直接广告变现。这种模式不仅吸引了大量受众,还倒逼广告预算向独立创作者倾斜。《华尔街日报》曾报道,2016年美国头部播客广告收入可达60多万美元。
在中国,视频播客能否复制这一路径?前证券分析师江东猫草认为,B站的流量激励可能推动行业“硅谷化”——最终留在舞台上的,或是像企业家这样“不靠广告挣钱”的群体,或是坚持内容品质的专业媒体人。Liz则观察到,视频播客放大了素人创作者的竞争压力,但也让优质内容更容易触达用户。在B站十亿流量激励的推动下,这种长视频对谈形式短期内仍将保持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