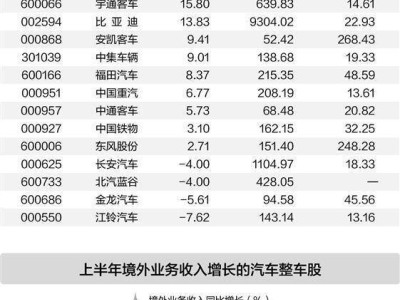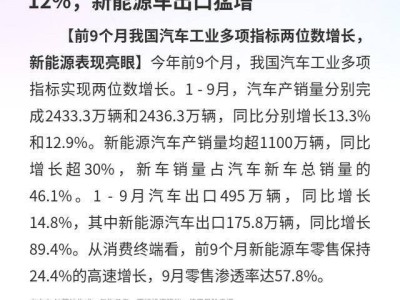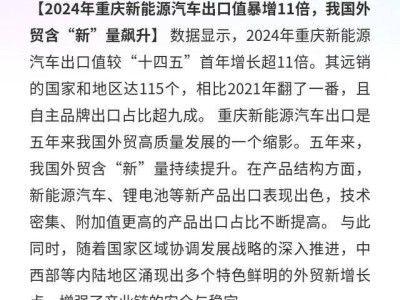新能源领域近日因一则合作消息掀起热议:京东联合广汽集团与宁德时代,宣布将于11月11日推出面向大众市场的“国民好车”。这款基于广汽埃安UT平台打造的换电改款车型,虽由三方共同推出,但京东明确表示不参与整车制造,而是聚焦产品共创、用户洞察及线上销售等环节。这场合作被业内视为平台企业重构汽车供应链的典型尝试,其核心逻辑并非造车,而是通过数据与渠道能力重新定义汽车消费模式。
京东的“下场”逻辑与电商行业格局变化密切相关。近年来,其核心3C品类增速放缓,百货领域又面临拼多多低价冲击,用户时长逐渐向内容平台迁移。尽管通过采销直播、百亿补贴等手段反击,但始终未能找到兼具高频、高价与高决策权的品类锚点。与此同时,用户结构呈现老化趋势:中产理性型用户占比过高,导致在即时消费场景中难以与抖音、快手竞争。而新能源汽车消费的长决策链、高客单价与服务周期长的特点,恰好契合京东用户的消费逻辑。
更深层的战略意图在于平台逻辑的升级。京东试图从“卖货”转向“影响供给”,通过“国民好车”项目掌握车型定义权。用户调研、配置偏好、价格敏感度等数据由京东平台先行收集,制造端据此反向优化产品。这种模式与其推动“京造”自有品牌的逻辑一脉相承,旨在成为连接用户需求与制造能力的“数字中枢”。据披露,该项目重构了汽车消费流程,消费者可灵活选择车衣定制、车品配装、养护加持等套餐,实现从选车到售后的一站式覆盖。
三方合作表面上是资源互补,实则暗藏角色博弈。京东的诉求在于掌控用户入口与消费话语权,通过绑定广汽与宁德时代构建汽车消费生态闭环——从选购、支付、试驾到换电、保养、金融的全链路服务均可在其体系内完成。对广汽而言,这既是去库存的低成本尝试,也是品牌年轻化的机遇,但主机厂对交付与售后的主导权并未轻易让渡。宁德时代则通过旗下时代电服输出换电技术与标准,试图将电池从一次性销售品转化为可循环服务资产,借助京东流量加速“电池即服务”模式的落地。
这场实验的复杂性远超营销合作范畴。尽管京东强调“轻资产”模式,不建工厂、不管交付,但仍需直面多重挑战。首先是品牌承接风险:公众可能将产品问题归咎于京东,尤其在“国民好车”命名下,品质与价格预期被推高,任何偏差都可能引发信任危机。其次是服务链条的重运营压力:汽车消费涉及维保、金融、换电等复杂环节,京东在试驾管理、线下服务网络等方面的经验尚待验证。更关键的是多方协同中的控制权模糊问题——产品周期、营销策略、用户责任归属等核心环节的权责划分仍不清晰。
从行业视角看,京东的合作代表了一种新型“平台造车范式”。与传统自建品牌、资本入股或技术驱动的模式不同,其通过用户数据与消费洞察积累整车定义层的影响力。这种模式在大模型时代具有延展潜力:AI可根据用户偏好智能生成车型,平台聚合制造资源完成商品化,甚至反向绑定主机厂成为“虚拟主机厂”。当汽车成为连接电商与能源服务的超级终端,造车最值钱的或许不再是车辆本身,而是决定其如何被消费的界面。
目前,京东已拥有近3000家养车门店、超4万家合作门店,并设立改装大店与自营贴膜工厂,形成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这些布局为其构建汽车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提供了基础,但能否将单次合作沉淀为可复用的平台能力,仍是决定这场实验成败的关键。当消费注意力持续稀缺,汽车作为继手机后的“超级入口”,正成为平台企业必争的战略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