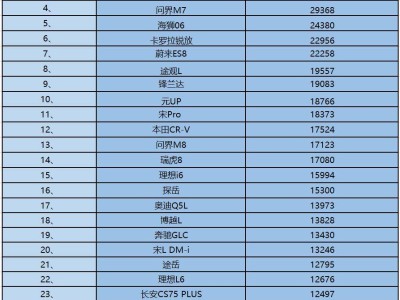在文创领域,一家以铜质工艺品为核心的企业正试图叩开资本市场的大门。这家名为铜师傅的公司,将目标客群精准锁定在30至55岁的男性群体,凭借平均客单价约750元的铜质摆件、雕塑等文创产品,在细分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被业内戏称为“中年人的泡泡玛特”。然而,与泡泡玛特所处的千亿级潮玩赛道相比,铜师傅所在的铜质文创市场规模在2024年仅16亿元,即便身为行业龙头,其营收连续三年也未能突破6亿元,赛道天花板清晰可见。
铜师傅的创业故事始于创始人俞光的一次消费经历。2013年,俞光计划为公司购置一尊铜关公像,却在市场调研中被120万元的标价震惊。当时铜材价格并不高昂,一尊雕像的原材料成本远低于售价,这种“普通人难以企及,少数人炒作高价”的行业乱象,让深耕制造业多年的俞光意识到传统铜工艺品行业供需严重脱节。行业模式僵化,手工打造效率低下、损耗大,多层经销商加价导致最终价格虚高。而俞光创办的雅鼎卫浴年出口额已突破2亿元,多年的制造业经验让他掌握了供应链整合与规模化生产的关键,他萌生了用工业品思维改造铜艺的想法。
2013年,“铜师傅”品牌正式注册,俞光的目标明确:打破行业暴利,让铜工艺品从少数人的收藏品变为普通人的家居装饰。他直接采用工业化替代手工的模式,将卫浴生产中的标准化模具、流水线作业引入铜雕领域。传统手工制作一件摆件需数周,而铜师傅的生产线仅需几天即可批量产出;手工损耗率高的问题,通过标准化生产将成本压缩至原来的三成。这种模式并非偷工减料,而是通过效率重构成本结构,其核心逻辑与小米的性价比策略如出一辙——只保留合理利润,将性价比做到极致。
俞光的创业理念吸引了资本的关注。作为资深“米粉”,他将小米的“专注、口碑、极致、快”七字诀改编为铜师傅的“降维、专注、极致、口碑”,并直言“小米不赚差价,我们也一样”。2017年路演时,俞光与雷军一拍即合。雷军看中的是用互联网思维改造传统行业的潜力,而俞光需要资本与资源的支持。顺为资本领投1.1亿元A轮融资,小米集团紧随其后,雷军更公开称赞铜师傅是“小米体系外最像小米的企业”。一年后,B轮融资3.1亿元,小米系继续追加投资,成为公司重要股东,助力铜师傅快速打通线上渠道、优化供应链。
俞光的“极致”不仅体现在商业模式上,更渗透到产品细节中。创业初期,他闭关三个月,砸毁上百个不合格模具,投入300万元攻克规模化生产的核心技术;为保证质感,每件产品需经过128道工序,表面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粗细;连包装都由他亲自设计,采用定制泡沫与硬纸盒,确保运输零损坏。这些细节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甚至有30%的用户在好评中提到“连发票都像艺术品”。
铜师傅的成长路径以“爆品驱动”为核心。2014年公司成立后,俞光并未急于扩张产品线,而是先推出“引流款”破局。2016年,售价19.9元的铜葫芦上线后迅速走红,单日吸引300万人关注,成为现象级爆款。这款产品持续热销多年,成为公司的“常青树”,也让铜师傅的品牌深入人心。同年,公司实现盈利,俞光顺势推动雅鼎卫浴登陆新三板,完成资本层面的首次尝试。借助小米系的资源,铜师傅快速拓展线上渠道,天猫、京东旗舰店迅速占据铜质文创品类销量榜首,线上收入占比很快超过八成。
尽管铜师傅在铜质文创市场占据领先地位,但其困境也源于赛道本身的局限性。整个文创行业看似广阔,但细分到金属文创,再聚焦到铜质品类,市场空间迅速收窄。铜师傅虽已成为这条“小池塘”中的最大“鱼”,但赛道的容量限制了其爆发式增长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其用户群体高度集中——核心客群为30至55岁的男性,他们购买铜师傅产品主要出于文化内涵与收藏价值的需求,消费理性且重复购买意愿较低。而年轻消费者对铜质摆件的兴趣有限,国潮风虽盛,但年轻人更倾向于为潮玩、美妆等产品买单,转化难度较大。
渠道方面,铜师傅主要依赖线上销售,线下门店布局稀疏。这并非公司不愿拓展,而是铜质文创的线下场景特殊:既无法像潮玩品牌通过门店体验吸引年轻人打卡,也难以像美妆品牌通过专柜试用促进成交。开设线下店的成本不低,但销量有限,因此难以像其他品牌那样密集布局。铜师傅还面临“上下夹击”的竞争压力:低端市场的小品牌通过降低材质标准、简化工艺打价格战,抢走价格敏感型客户;高端市场则有黄金、银质文创产品分流送礼与收藏需求,部分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保值性更强的贵金属;跨界来看,泡泡玛特等潮玩品牌也在争夺年轻消费群体的预算。
尽管如此,铜师傅仍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公司掌控从设计到生产的全链条,成本低于同行;拥有大量自主设计的IP,无需依赖外部授权;线上渠道的先发优势积累了忠实用户。然而,小池塘的天花板触手可及,铜师傅不得不尝试“破圈”,探索塑胶潮玩、黄金文创等更大市场。但这些领域已有成熟玩家,且铜师傅的客群定位与年轻消费者、女性消费者的需求存在错位。其擅长的“文化内涵+高性价比”模式,在潮玩与黄金赛道中可能难以奏效——年轻人购买潮玩注重IP共鸣与社交属性,女性购买黄金看重设计与保值性,这些都是铜师傅的短板。
铜师傅的上市之路充满波折。2022年,公司启动A股创业板辅导,市场曾期待其成为“铜文创第一股”。但A股对企业的要求不仅包括盈利能力,还需具备快速增长潜力,而铜师傅所在的16亿元规模赛道显然难以满足这一条件。2024年,铜师傅终止A股辅导,转而冲刺港股。港股更看重企业的行业地位与商业模式清晰度,对短期增长速度的要求相对较低。尽管铜师傅作为行业龙头盈利稳定、模式易懂,在港股具备生存空间,但其估值却面临“打折”——市场对小众赛道天然谨慎,且港股投资者更偏好规模大、成长快的企业,铜师傅这类“增长慢、赛道小”的公司难以获得高溢价。文创企业的估值核心在于IP,而铜师傅的IP逻辑与资本青睐的模式存在差异。
资本偏好的IP需具备高复购潜力,如泡泡玛特的盲盒产品,其随机性与潮流感激发消费者凑齐整套的欲望,形成持续现金流。而铜师傅的IP多源于传统神话与民间故事,消费者购买后主要用于装饰或送礼,重复购买需求较弱。简言之,泡泡玛特的IP是“社交货币”,年轻人购买后会晒在社交平台形成传播;而铜师傅的IP是“生活摆件”,购买后多置于家中,难以产生二次传播与复购。这种差异导致两者在资本眼中的价值天差地别。
为改变现状,铜师傅尝试推出新自研IP并寻求热门IP合作,以吸引年轻消费者,但效果有限,合作IP带来的收入始终未成为增长主力。问题不在于IP数量不足,而在于变现场景单一。同样是传统文化IP,三星堆文创可延伸至文具、美妆、潮玩等领域,覆盖更多生活场景;阅文的小说IP可改编为电视剧、游戏并推出衍生品,实现多维度盈利。而铜师傅的IP无论自研还是合作,最终多以铜质或塑胶摆件形式呈现,场景未被打开,IP价值难以提升。对铜师傅而言,上市并非终点,而是解决增长问题的起点。港股虽能提供融资,但能否实现估值修复,仍需解决两大核心问题:一是让IP摆脱“摆件依赖”,拓展至更多生活场景;二是打造能持续吸引用户的爆款IP,提升复购率。若能突破IP场景限制,适配更广泛人群,铜师傅或可跳出小众赛道的估值陷阱;若仍困于“摆件”领域,即便成功上市,也可能仅是换了个市场,继续面对增长焦虑。港股为其提供了资本化舞台,但最终表现仍取决于自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