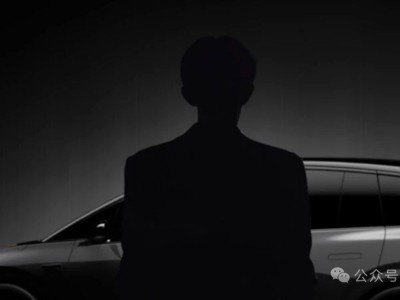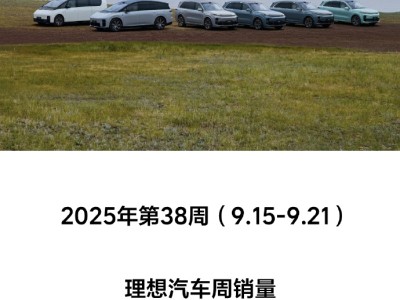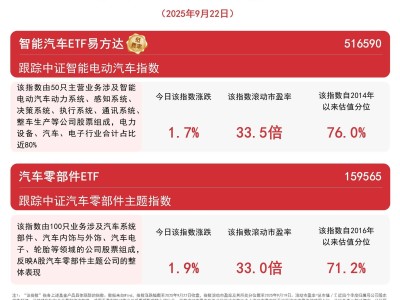近年来,中文播客市场经历了从边缘到主流的跨越式发展。曾经被视为小众爱好的播客,如今已深度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商业数据平台Statista预测,2024年中文播客听众规模将达1.34亿,相当于每100名互联网用户中就有12人定期收听。《2024年播客行业报告》进一步显示,76.2%的用户每日收听时长超过半小时,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军。
头部平台的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截至2024年底,喜马拉雅月活跃用户达2.8亿;B站凭借中长视频生态,早在2021年便试水“沉浸式听视频”功能,并推出播客专区;专注播客的小宇宙App日活跃用户突破250万,平台节目总量超10万档,涌现出《凹凸电波》《不合时宜》等热门节目。然而,行业繁荣背后,商业化困境日益凸显。
今年4月,头部节目《不合时宜》被曝拖欠工资,引发行业对盈利模式的讨论。节目方回应称,2024年3月至11月广告市场低迷,仅完成一单商业合作,主要收入依赖会员计划“不合时宜全球成长计划”,扣除成本后净收入约13万元。这一案例暴露了中文播客“叫好不叫座”的普遍问题:用户规模持续增长,但创作者难以实现可持续经营。
在此背景下,视频播客被视为破局关键。传统播客以声音为媒介,通过通勤、家务等场景提供陪伴感,而视频播客通过添加面孔、表情与场景,增强了情感传递与信息密度。例如,B站今年7月推出《视频播客出圈计划》,提供10亿级流量扶持、免费录制场地及AI工具,吸引音频创作者转型。8月,平台签约杨迪、罗永浩、鲁豫等明星,推出《迪听》《罗永浩的十字路口》等节目,单期播放量达数百万次。
小红书则以更轻量的方式切入。8月,平台发起“随时随地视频播客”活动,鼓励用户发布15-20分钟横屏视频,讨论“我的天才朋友”“我的专业故事”等话题,优质内容可获5-30万流量曝光。抖音、喜马拉雅等平台亦纷纷试水:抖音精选联合JustPod推出《精选奇遇记》,探讨职业与旅行话题;喜马拉雅5月推出视频化节目《行走的思考》,50天播放量破千万。
视频播客的兴起,反映了平台对“中视频”赛道的争夺。B站的策略尤为系统化:除流量扶持外,还设立精选栏目,提供创作指南,并在一线城市搭建专业录制棚。这一布局旨在填补1-10分钟短视频与45分钟以上长视频之间的空白,满足用户对深度对话的需求。同时,通过“音视频一体化”生产模式,创作者可将原始素材剪辑为视频、音频、短视频切片等多形态内容,实现全平台分发。
例如,杨天真的播客《天真不天真》采用同期录制,素材经剪辑后适配B站、小红书、小宇宙等平台。这种“一鱼两吃”的策略,使视频播客成为内容素材库:视频母带用于长视频平台,短视频切片用于引流,音频源满足原教旨听众需求,关键信息提炼为金句占领笔记类平台。泰勒斯威夫特视频播客切片在TIK TOK的传播裂变,以及B站明星节目切片引发的全平台讨论,均印证了这一模式的潜力。
国际市场的经验为国内平台提供了参考。Spotify自2020年推出视频播客功能后,用户规模持续增长,至2023年6月已有超1.7亿人观看过相关内容。美国市场中,明星与网红开设视频播客已成为常态,头部音频节目同步推出视频版更是标配。这种趋势与家庭大屏场景的回归形成契合:YouTube用户每月在电视端观看视频播客的时长超4亿小时,B站亦在页面强化电视端引流提示。
尽管视频播客为行业带来了新机遇,但其发展逻辑与美国存在差异。它不太可能成为颠覆性媒介,而更可能作为音频播客的“超级赋能工具”,通过视觉化提升内容维度,在社交媒体撬动流量,并深化创作者与粉丝的连接。对平台而言,这是抵御短视频冲击、探索大屏场景增量的尝试;对行业而言,视频化拓展了品牌植入、衍生直播等商业化想象空间。